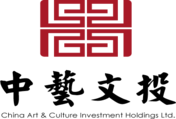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神话认同
2018-01-17 16:16:00 来源:中国民俗网 已浏览次
造成民族融合的因素很多,有政治经济联系加强的原因,也有种族血缘混同的缘故,而文化的认同却更为重要。文化认同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其中哪一款最引人注目,能从根本上消除种族间的壁垒,成为民族融合的标志性事件呢?德国哲学家谢林有一段话颇令人回味:“一个民族,只有当他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为民族时,才成为民族”。 他敏锐地觉察出:神话是文化传统的核心支柱,认同了一种神话也就认同了一种文化,栖居在一种神话所营造的文化母体之中,也就意味着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一员。一旦共同文化母体孕育成型,民族便呼之而出。
民族是相对稳定的文化群体,但始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会引起集团的扩张、缩小或者离散。民族融合是已经成型的民族的重组,无论是被融入的一方还是融入的一方,新的民族都不与先前完全一样。但这种融合又不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的成分分摊,它是带着自己的优势向另一种优势文化的皈依,假如一民族成员觉察出自己文化的弊端,向优势文化看齐而不惜抛弃固有文化的部分内涵,实是民族文化发展重要途径,因为一成不变的文化最终要走向覆灭。被融合方不是被对方吞噬,相反是对一种新的传统的占有,使自己获得养分而壮大。各种文化传统都是资源,明智的民族取之发展自身,反之则会遭到淘汰。
中华民族自先秦两汉时代传下一批文化典籍,它是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夏商秦汉各族群体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本。在东方世界,它是除佛教之外的最大的文化资源。先秦两汉时期典籍所记录的神话系统与祖先谱序成为中华民族归向的标尺,是所有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各族人民在享用这份文化遗产时实现了真正的民族融合。北朝时期,北方各族投入中华民族的怀抱,均将接受先秦两汉文化典籍作为前提。其中,认同神话成为标志性事件。
一、共同的帝王神话模式使北方各族在政治神话上与
秦汉典籍接轨,构成了一种典型的统治者的神话模式
北朝的主流神话是拥有中央政权的民族统治者的帝王神话,虽其内容与传统的中原神话有异,然其性质和结构模式与中国原神话悉同。从性质上讲,它只是秦汉以及先秦帝王符瑞神话的变种,它夸张帝王出身的神异以示其非同寻常,系神权天命来接受政权,故从本质上讲它是政治神话,对其王朝的存在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就其结构形式看,它同于远古中华图腾神话的模式,往往由其母与神物相交相感而生。其最近的源头,乃是纬书中的感生神话,北方诸民族政权的帝王神话,可视为感生神话直接影响的产物。
北汉刘渊为匈奴人冒顿之后,汉初时高祖妻宗女于冒顿,约为兄弟,故子孙姓刘。三国时曹操分其部为王,活跃于西北。刘渊父名豹。关于刘渊的出身,有这样的神话:
豹妻呼和浩特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髻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祥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从邯郸张冏母司徒氏相云,吾当有贵子孙,三世必大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晋书·刘元海载记》
此一故事,脱胎于传统神话及纬书故事迹象甚明。刘渊长而好《毛诗》、《易》、《尚书》、《春秋左氏传》等经书,《史》、《汉》诸子,无所不览,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很深,传统神话融于心灵之中。像京氏易这类充满神秘色彩的典籍的影响,是他编造神话的源泉。鱼与日精之瑞,于史书和纬书中多有,它是同神话的变种。
司马迁于《史记》载有白鱼赤乌神话,其文曰:“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史记·周本记》)今文《尚书》、《尚书大传》之《泰誓》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载。白鱼赤乌神话不见于先秦文献,殆汉神话,它在汉时广为流传。《汉书·董仲舒传》引《贤良对策》云:
《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
若依五德相克说,白鱼指殷之金德,而赤乌为周火德,以火克金,白鱼入舟只是殷亡之征,而赤乌现世才是周的符瑞。然而,在流传中,白鱼同赤乌并为符瑞了。从《史记》到各种纬书记载,白鱼赤乌都是符瑞。且白鱼化为赤乌,二者融为一体。刘渊的符瑞神话脱胎于感生神话并取纬书母题以充实发展之,这是刘渊汉政权承接神话文化传统的一座桥梁。
此类神话在北方民族政权的统治者身上屡屡发生。如刘渊子刘聪,其出生也甚奇特。《晋书·刘聪载记》:“初,聪之在孕也,张氏梦日之怀,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征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聪焉,夜有白光之异,形体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长二尺余,甚光泽。”此感日而生之神话乃其父日精所生的衍化。匈奴中有拜日的习俗,《史记》称其好“拜日之始生”,这是匈奴的传说,他们在传统的感生模式里装进了自己的内容,故刘氏匈奴的神话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当然拜日习俗不为匈奴所独有,周秦以来的祀典都把拜日放在重要位置,所谓郊祀祭天的核心是拜日。《礼记》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匈奴俗之拜日跟华夏传统郊祀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为匈奴与华夏本有文化与血缘联系,《史记》称匈奴为夏后氏芮裔不是空穴来风。
关于刘聪感日而生的神话,也是来自纬书。《河图著命》:“扶都见白气贯日,意感生黑帝子汤”。这种神话不仅模式相同,内容也近似。匈奴本来就有与华厦相仿的崇日习俗,而神话制造的模式也一样,这样就造成了政治神话与华夏文化同宗。刘氏匈奴的帝王神话,多仿五帝三王神话,如关于刘曜的传说,史书载刘曜“年八岁,从元海猎于西山,遇雨,止树下,迅雷震树,旁人莫不颠仆,曜神色自若”。此与“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相类,至于刘曜的种种传奇及符瑞,也大多脱胎于汉纬书神话模式,体现出匈奴与刘汉政权之间不可分割的文化联系。
我们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神话作一排比,发现其主流已不是原先的民族神话。他们过去的图腾神话已经转变为中国传统的帝王感生神话:
慕容德,鲜卑人,南燕皇帝。“母公孙氏梦日入脐中,昼寝而生德”。
——《晋书·慕容德载记》
拓跋珪,鲜卑人,北魏皇帝。“母曰献明贺皇后,初因迁徒,游于云泽,既而寝室,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歘然有感。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其夜复有光明”。
——《魏书·太祖记》
北方民族的统治者如此热衷于编造帝王符命神话,原因在于这些民族在中原统治区内、夷夏交织杂居,他们开始在中原建立政权,文化根基尚浅,便不得不以神话强化其地位。一方面,这些汉人已习以为常的模式会使人产生亲近感信赖感,而少数民族又本信鬼神,其习较汉民更重,这些神话使对其主不得不更加顶礼膜拜之,使统治者政权力量得到神话的支持。
神话形式的仿造也带来了内容的重演,一定的模式是依凭一定的内容建立起来的,帝王神话袭用了远古先祖与图腾神话的外衣,使帝王跟神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神话已经不是纯粹的图腾神话,它受到汉典的史籍及其经典纬书的影响很深。如果说远古先祖与图腾的神话是为树立氏族的宗神而使民众产生心理向力的话,帝王的神话便是宣扬君权神授,宣告百姓应理所当然服从统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神话是对传统统治思想与方略的一种继承,显示出少数民族政权向共同文化的皈依。帝王与统治者的神话是社会的主流神话,当北方民族政权袭用传统的政治神话模式时,便标志着社会的主流文化趋向统一。
二、选择共同的祀典标志着北方民族站到中华文化的同一神灵庇护所下
当北朝统治者与南朝统治者采用共同的祀典时,便预示着南北文化的统一。中国古代的皇家祀典自商周开始形成而于秦汉趋于成熟,是各族统治者和人民广泛认同的范本,拥有它就是拥有对神灵的垄断权和对社会的主导权。天地、社稷、祖先、日月、山川、风伯雨师之神是整个社会文化统治的主宰。北方神话对传统神话认同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面对共同的神灵,尊奉同样的祀典。它需要抛弃种族地域色彩很重的旧神,因而,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
北方民族统治政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仅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是觉得自己是整个天下的主人。他们建立政权起初是同南方他庭抗礼,最终目的是统一天下,而统一天下的文化是中原传统文化。所以,北方政权大多自称“中国”,而称南朝政权为“逆乱”,其征伐的目的是显“中国之威”,他们追求的是统一大业。正是由于这种境界,北方的少数民族形成了大融合的态势,他们自觉地遵奉商周以来的皇家祀典和秦汉以来的五帝德运,是中国传统的真正主人。
刘渊在称帝前有这样的宣言:“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尔?”(《晋书·刘元海载记》)他认识到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并不是种族中心论而是道德决定论,这是周公以来尊天敬德观念的发展延续。刘渊高举德统大旗,历数司马氏父子的罪过,又借助汉室宗亲的身份,这不是一个代表匈奴种族的政权,而是一个人以继承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面目出现的政权。《晋书·刘元海载记》云:“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以“僭”贬之,显示出民族观。然而,我们从这段记载中看到,刘渊为坛南郊,承《礼记》《周礼》的祭天传统,把握了皇家祀典的核心,表明自己是一个继承华夏文化传统的正统王朝。
鲜卑慕容生于幽漠,当他作了燕皇帝,便告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他建立的是一个“中国”政权,而不是割据一隅的独立王国。关于大燕的历数,臣下已这样安排:“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 载记》)燕承袭五德转移学说,以金生水,承晋金为水德,与中原五德转移学说接上了轨,成了“正宗”的帝王。
前秦符坚是北朝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是对传统文化颇为醉心者。他说:“帝王历数岂常哉,惟之所授耳!”他向往一统天下而封天禅地,他始终以中国正宗之位居之,而称“东南一隅未宾王化”,时时计划引兵讨之。朱彤一席话让符坚心潮激荡:“陛下应天顺时,恭行下罚,啸咤则五岳摧覆,呼吸则江海绝流,若一举百万必有征无战……然后四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符坚听后大悦说:“吾之志也”。朱彤构画的夺取天地后,以成功告天地,然后受命于天,成万世之功业的蓝图,使他成为一个自豪的天神之子,所以他对传统的受天大命之典心向往之。
北魏政权建立后,其祀起初是一个周秦传统的祀典与鲜卑民族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周秦祀典。《魏书·礼志》:
太祖(珪)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帮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祭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
很明显,拓跋珪一称帝就归入了皇天后土的麾下,这是中原古来天子的共神;而继黄帝之后,不仅意味着种族认同,更是帝德传承,于是北方中国有了一个强大的“正统”政权。
但早期祀典中颇多鲜卑旧礼,如郊天,太祖西郊,则与周秦祀典之南郊不类,但天兴二年便转为“亲祀上帝于南郊”,把原先对西方故乡的恋情也割断了。又如祭坛上的神灵,原从食者有一千余神,可谓杂乱,且多为胡神。孝文帝厉行汉化政策,祀典据《礼记》费了一番斟酌。他要求祀典合力于古礼,曾召集臣下讨论《礼记·祭法》篇及郑、王注文异同问题,这种严肃的态度表明孝文帝是要在祀神大典上绝对合于传统,做到“有文可据,有本可推”,这“文”这“本”都是指儒家经典。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下诏:“国家自先朝以来,饷祀诸神,凡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魏书·礼志》)他汰去的小神是民众普遍祭祀的神灵,而留下的仅能传统祀典中的神学骨干,祀典真正归于“正典”了。
孝文帝还主持一场规模盛大的帝德讨论,这是关系到国家接受怎样的文化传统,关系到南北对峙的历史哪一方是正统的问题。有趣的是,北方同南方一样,都把自己列为正统,斥责对方为僭伪。这种观念虽然自我中心色彩甚重,且对抗性强,但双方都把自己列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都向往着大一统天下,这正是民族精神的可贵之处。北魏政权认为自己是正统是没有疑义的,但帝德是承前秦之后,还是承晋后呢。当时高阊等人的滔滔宏论,显示出对中原神话传统的精深研究与把握。孝文帝从实行汉化的立场出发,选择承晋金为水德,是又一种神话接轨。
北朝各族政权采用传统祀典接受五德转移学说,将南北统一在共同的神祗之下,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三、皈依同一祖先 南北同为炎黄子孙
北方民族融合是以认同共同的神话先祖为最终标志的。祖先本为一族的血缘标记,可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识别,与真实血缘统系无涉。认同同样的天地神祗并不能表明是同一种族,而共奉祖先却毫无疑问是认为同为一家。中华民族的统一不是种族血缘的统一,而是文化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祖先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血缘之祖,而只是一种文化之根。中国民族神话的核心有两个:龙与黄帝,后者更为重要。以黄帝为核心的五帝系统是各种族对中华民族归向的标尺,它集中体现为礼书之五帝德与帝系及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建立的古代先祖谱系。这个谱系既是一座熔炉也是一个磁场,它敞开胸怀拥抱着投奔者,一旦被接纳,每个成员都打同样的标记,每个人都会以背叛这伟大的先祖而羞耻,并以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而自豪。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对后来匈奴的发展具有难以估量影响。夏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是黄帝为中心的五帝系统的正宗嫡传。司马迁这样写肯定是有传说和记载作为基础的。匈奴后来与汉室通婚,双边关系更进一步密切。汉与匈奴尽管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但和平的力量始终在起作用。因为有禹后与汉宗亲两个重要历史渊源,汉匈间的融合变得十分自然。从前者看,汉匈是兄弟,从后者看,汉匈是亲家。所以,北朝时匈奴各部与汉融合都是基于以上两个前提,其中一个是事实,一个则是神话传说。
刘渊是典型的打着汉室宗亲旗号的匈奴贵族。他认为,没有汉人的拥护,尽管实力强大,也是难以称王的。他说:“没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乐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故不建匈奴政权,而建汉政权,泯灭汉匈界线,理直气壮地作了天子。
刘氏匈奴之后,铁弗匈奴一支的首领赫连勃勃不满于刘渊以汉朝为是,他要绍夏后氏之统,故“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他雄心勃勃,说“朕大禹之后”,要“复大禹之业”。(《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赫连勃勃口不离大禹,言不舍大夏,仿佛大夏王朝的基业,在经历夏桀之败之后又复兴于北方。赫连氏熟知华夏古史,其作答刘裕书,使南朝皇帝自叹不如。铁弗匈奴不仅自称为华夏儿女,同时是华夏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与匈奴一样,鲜卑在北朝时期也融入中华民族群体之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是北朝时鲜卑强姓。慕容氏起于辽河流域,《晋书·慕容廆载记》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显然他们自认为黄帝子孙。西晋末年,酋长慕容廆受晋爵位,为晋藩属。永嘉乱后,慕容廆跃跃欲试,说:“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系。孤思与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晋书·慕容廆载记》)这时的慕容氏,完全将自己视为天下兴亡而有责的“匹夫”。慕容氏后建燕国,要“侔迹虞夏”显然是以华夏儿女的身份又去接受华夏文化。
拓跋氏则直述其为黄帝之后。《魏书·序纪》云:“昔黄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孝文帝与群臣讨论帝德时,都强调魏是“祖黄制朔,緜迹有因”(《魏书·礼志》),表示自己是黄帝传人。就连拓跋姓氏也跟黄帝相关。“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礼志》)
拓跋氏鲜卑强调其祖先为黄帝,表明他们向往着华夏文明的博大,并自觉地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北魏的几代皇帝都到桥山黄帝陵祭奠,而自己在大鲜卑山(即今天大兴安岭)的老祖先的庙都要忘掉了。他们不仅祭黄帝,并修尧、舜、禹庙。孝文帝不好鬼神,并屡禁杂祀,但他对五帝抱相当热情,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孝文帝厉行汉化政策,包括汉姓、汉语的使用及与汉通婚,拓跋氏鲜卑与汉无论是文化上还是血缘上都完全融为一体了。
宇文氏鲜卑自称炎帝神农氏之后,(《周书·文帝纪》)这完全将自己置于炎黄子孙的地位,其政权命名为周,是绍周秦之统。宇文氏的汉文化,标志着鲜卑与汉两族的全面融合,产生了活跃隋唐时期的新的汉族种群,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异常强劲的活力。
以上我们考察了北方匈奴、鲜卑两大民族融合到整个中华民族之中的过程,发现神话的认同与归宗乃是民族融合的关键。撇开带有准宗教性质的孔子崇拜不谈,传统典籍的神话对北方民族的影响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史记》、《汉书》及纬书中的帝王感生神话与五德转移模式成为了北方各民族的统治者自我神化所遵奉的蓝本,带来了共同的君权神授的政治神话;二是《尚书》、《周礼》和《礼记》中所记载的祀典,对这套神谱的认同表明北方各族的统治者已跟汉统治者站在同样的神灵庇护所下;三是《大戴礼》及《史记》所载的以黄帝为中心的民族先祖谱系,认同它便是同种的象征,表现出人们已归入了以黄帝为核心的祖先谱系的民族文化团体之中。
北朝时期的民族文化认同是以传统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内向认同,它是中国神话的一次内聚,北方各族相继以中原古神话为准的作精神皈依,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运动。神话与民族融合的内在联系,在这场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
田兆元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