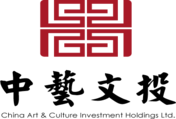藏族《格萨尔》在土族和裕固族中的流传与变迁
2018-03-21 14:14:57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已浏览次
摘要: 藏族史诗《格萨尔》今日在土族和裕固族中广为流传,但在早期这些民族中却是禁唱《格萨尔》的。历史上曾有格萨尔和霍尔王交战、霍尔王战败被格萨尔所杀的故事,所以在土族和裕固族中说唱《格萨尔》会使霍尔三兄弟(即指黄帐王、白帐王和黑帐王,分别是裕固族、土族和汉族的祖先)不高兴。时过境迁,现在土族和裕固族中不仅说唱、流传着《格萨尔》,而且人们还产生了特有的社会历史心性和追寻英雄祖先的意识。
关键词: 格萨尔;土族;裕固族;流传与变迁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创作的英雄史诗。这部不朽的著作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早在吐蕃王朝时代,《格萨尔》就已传播到喜马拉雅山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大约在13世纪以后,随着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大量藏文经典和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蒙古文,《格萨尔》也逐渐流传到蒙古族地区,成为自成体系的蒙古族《格斯尔》。14世纪下半叶,即元末明初,《格萨尔》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据调查报道,藏族《格萨尔》在中国相继流传到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纳西族、白族、普米族、摩梭人等兄弟民族当中,且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与各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各具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格萨尔》[1].但是《格萨尔》流传到这些民族中的过程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顺理成章,而是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在此以土族和裕固族为例。
一
今天藏族史诗《格萨尔》在土族和裕固族中广为流传,但在早期土族和裕固族中是禁唱《格萨尔》的。土族中普遍流传他们是班嘎尔三弟兄的后裔,历史上也曾有格萨尔和霍尔王交战、霍尔王战败被格萨尔所杀的故事,说唱《格萨尔》,霍尔三弟兄不喜欢。霍尔三弟兄,即指黄帐王、白帐王和黑帐王,土族人说这是他们的先祖,现在佑宁寺之左河旁还修有霍尔三弟兄的宫殿,有些土族人家还立有他们的神位来供奉[2].
土族学者李克郁教授介绍说:“记得1944年,也就是在我9岁那年,父亲用自己多年的积蓄盖了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子。因为是新房子,里面的板壁需要油漆,并要作画装潢。因此,父亲要哥哥和我一同前去请木拉霍尼其(mulaa huniqi,小羊圈)的画匠……这位画匠的名字叫官布希加……官布希加来到我家,大约有两三天时间。有一天晚上,也就是第三天的晚上吧,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村里的大人们一个个来到我家里,大约有十来个人。乡里人有个特点,平时串门闲聊,总是大喊大叫的,可是这天晚上很反常,他们一个个不声不响,悄悄地进了新盖的那座房里。
我家院子的中心点上,有一座用土坯砌成的台子,周围是喂养牲畜的槽,所以,这个土台子叫做转槽或圆槽。转槽的中心点是个高约三丈多的旗杆,旗杆顶部飘着印有经文的幡。旗杆根部的南侧,是高出转槽约三尺的香炉,也是用土坯砌成的。这里是我百岁祖父每天早晨烧香磕头的地方。
等到人们来齐的时候,已是夜深人静了。父亲从屋里走了出来,煨了桑、烧了香、磕了头,然后又悄悄进了屋,把门反插上,弄得有些神秘。我和哥哥觉得很奇怪,于是踮着脚不声不响地走进窗根,听大人们究竟在议论什么?原来画匠官布希加在给大家讲故事,时而在低声唱着,时而在讲述着。我站在窗根下,耳朵贴在窗户上,还是听不清楚。可是在他唱曲调时,总是嗝日嗝(girigi),嗝日嗝的。从此,我们给了他一个绰号,叫做嗝日嗝,再也不叫他画匠或官布希加了……
后来,我们问父亲,嗝日嗝讲的是什么故事?为什么弄得那么神秘?父亲说:“嗝日嗝讲的是格赛尔的故事,佛爷不准在蒙古尔(土族自称)当中讲这个故事。我烧香磕头是为了忏悔自己的罪过。”[3]
同仁土族也认为,自己与霍尔有密切关系。郭玛日人说,泽库县霍尔哇加保存着他们的历史,根子在霍尔。当初霍尔人住在这里,一半留在这里成为土族,另一半到了泽库,霍尔杰岗是首领。他们信霍尔,不信格萨尔[4].
同样,在裕固族中间也有类似的说法。在裕固族的历史传说中认为,黄帐王是裕固族可汗。①俄国探险家波塔宁(Potanin)在其著作中说:“某些裕固族人声称霍尔黄帐王才是他们真正的国王。”而且指出他在裕固族人中发现了“霍尔黄帐王很多马和犬。②著名藏学者松巴·堪布益喜幻觉尔(1704年—1788年)在给第六世班禅白丹依喜(1737年—1780 年)的复信(又称《问答》)中指出:“在距青海湖北面7、8天的路程,有一个叫巴董(pa—stonk),有一河名叫熊暇河(shunk-shai-chu),从这里到汉族肃州城(rkyisu-kru-mkhar)的土卡(thurkha)之间有所谓的霍尔黄帐部,此亦即所谓撒里畏吾尔(shara-yu-kur),又称‘班达霍尔’(vpan-t-hor),还称‘霍屯’(hor-thon)”。③由此可知,他认为霍尔黄帐部就是撒里畏吾尔,即元、明时代裕固族的名称。另外,他还认为霍尔白帐部是“索波人”(sok-po),即蒙古族。黑帐部是“卓博”(vprok-pol),即藏北胡系统藏族牧人。有学者认为,“松巴堪布身为蒙古人,又久居蒙藏交错杂居的青海地区,很熟悉这一地区的各民族情况。他对甘青一带各民族的考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5].同样的看法也见于现代著名藏族老学者毛尔盖·桑木丹的论著中,他不仅认为霍尔黄帐部就是裕固族,而且认为“撒里畏兀儿”(sh-Aurke)是蒙古语黄帐之意[6].裕固族最后一任大头目安贯布什加,曾对中国科学院社会历史调查组说,我们是霍尔[7].过去,裕固族有敬奉“汗点格尔”的原始崇拜,不论是操西部裕固语的人,还是操东部裕固语的人,都称作“汗点格尔”。但是,当地藏族称之为“霍尔泰”,意为裕固人的神[8].
对裕固族而言,史诗主人公格萨尔既是英雄又是仇敌。例如,裕固族地区流传的其他《格萨尔》故事中有这样的内容:“像日月一样尊贵的客人,请允许我讲一段故事——英雄的格萨尔。格萨尔世代传颂的英雄,他恰似山中猛虎,犹如海底蛟龙。捧起海子水般的醇酒,也无法表达对格萨尔的崇敬。但他杀死了尧乎尔(裕固族)的可汗,在我们祖先的心中,也曾产生仇恨。相传在过去,但凡尧乎尔子孙,在格萨尔王庙门前都要停步:抽出刀剑对他挥舞,还要用吐沫啐吐。这是尧乎尔早先的风俗。”[9]罗列赫在其著作中特别指出了裕固族(黄西番)中一些人会使人联想到《格萨尔》史诗的风俗习惯。例如,某人骑一匹枣红色的马接近一顶帐篷,那就要把马拴起来,使其头转向该地区以避免具有同样颜色的格萨尔之马再出现并以其蹄蹋平帐篷。裕固人吃饭吃得很快,因为他们声称格萨尔的一次奇袭使他们至今仍感到惊怕。大家声称在他们之中存有《格萨尔》史诗的另一种文本。其中奉霍尔人国王为其祖先,而格萨尔可能是作为危险和狡猾的敌人之面貌而出现的。罗列赫由此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所以,对于古代的吐蕃和突厥部族之间爆发的部族之战的记忆至今尚存在,成了经常性的部族冲突的原因。”[10]
据大多数《格萨尔》研究者认为,格萨尔的故事并非虚构,历史上实有其人其事,而且认为故事中的格萨尔就是角厮啰,①黑霍尔就是蒙古游牧部落(黑鞑靼),白霍尔就是靠近汉区的农业部落(白鞑鞑),黄霍尔即黄头回纥。而且在宋朝,党项人经常勾引鞑靼、回鹘壮大自己的势力,并征调他们与角厮啰进行了长时期的战斗。格萨尔与霍尔三国的斗争,实际反映的是党项西夏与角厮啰之间的争斗[11].
由上述可知,历史上的格萨尔是土、裕固民族的敌人,他给两个民族的先民留下了可怕的记忆,土族和裕固族的先民是忌讳说唱格萨尔的。
二
时过境迁,现在土族和裕固族中是允许说唱和流传《格萨尔》的。虽然土族在说唱《格萨尔》之前,一般要煨桑,求霍尔王不要发怒,允许他们说唱《格萨尔纳木塔尔》;但是年轻的说唱者已经不继承这种习俗了,他们已不相信神祖会发怒。有的说唱者甚至对岭王和霍尔采取不褒不贬的态度,有的还认为格萨尔是英雄,救了我们,我们可以赞颂他等等[12].在1948年,从一个47岁的土族艺人口中可以记录12000行土族《格萨尔》史诗[13].50年后,从一位老艺人口中仍能搜集整理出500万字左右的土族《格萨尔》[14].由此,我们可以想像《格萨尔》在土族地区流传的盛况。《格萨尔》在土、裕固族中的这种变迁,也与甘青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变化,藏族和土族、裕固族形成了毗邻、杂居的局面,同时又都信仰藏传佛教,共同的宗教信仰势必导致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据介绍,过去在互助、民和以及其他土族聚居区,寺院林立,僧侣众多,素有“三川的喇嘛遍天下”之说。土族僧人一进寺院就学藏文,这样,僧人便有了接触并传播藏民族文化的机会[15].
在裕固族地区调查到的20多位《格萨尔》艺人,多数会说藏话,有的懂藏文,其中有些是本人或是他们的前辈是寺院的僧人。如73岁的扎巴尼玛唯色就曾当过互助郭隆寺下属一寺的班弟,他说唱的《格萨尔》是用藏语吟唱韵文,然后用东部裕固语来解释。通婚也为格萨尔在土、裕固民族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例如,裕固族有位艺人名叫赵嘎布藏,他原系藏族,久居青海祁连蒙、藏、土、裕固等民族杂居之区,会说东部裕固语,1958年迁居肃南皇城区北滩乡。他除了会说“乔冬外出做买卖亏本”“当岭王国家衰败”等片断外,主要说唱《阿古叉根史》《阿古乔冬史》和《安定三界》等。他当年70岁,在他26岁时当了一位裕固族人的上门女婿。他除了在家里说唱外,还经常给裕固族群众说唱《格萨尔》,颇有名气[16].
三
总之,像土族和裕固族这样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在甘青地区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中不断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当中,有些是被动的,是被历史大潮裹挟而去的;有些貌似主动,其实也是无奈的。例如土族和裕固族传唱《格萨尔》的过程,表面看似主动接受,实际也是无奈之举。在主流社会或周边其他强大民族的威力下,当地方历史或族群文化表述的权力被取缔、记忆被消除,出现结构性失忆时,被结构压抑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就会在这种展演中得到张扬,尤其表达了对地方历史或民族文化表述的关怀。在展演中,历史情感会得到理解,同时也会唤起民族的尊严。一种结构性社会情境会产生特有的、可支持此社会情境的历史心性。然而历史心性本身只是一种“心性”,一种文化倾向;它只有寄托于文本,或某种文类中的文本,才能在流动的社会记忆中展示自己。因而历史心性所产生的主要是文本(或表征)。文本与文本间的模仿、复制形成文类。文类结构中蕴含着历史心性[17].因此,在土族和裕固族的《格萨尔》故事中蕴含着一种英雄祖先的历史心性,是小族群对“我者中的他者”的一种暧昧、扭曲,或矛盾的记忆。
参考文献
[1]李战吉。《格萨尔文库》问世[N].人民日报,2001-02-11(1)。
[2][12][16]王兴先。土族史诗《纳木塔尔》述论[A].格萨尔学集成(第 2 卷)[C].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943.
[3][13]李克郁。土族格赛尔[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2-3.
[4]青海省编辑组。青海土族社会历史调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176-178.
[5]如意宝树史·序(汉译文)[Z].蒲文成,才让泽。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6]毛尔盖·桑木丹。格萨尔其人[J].章恰尔,1985,(4)。
[7]吴永明。关于“裕固族简史”补充调查和修订工作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动态,1983,(4):19
[8]《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30.
[9]郝苏民。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270.
[10]石泰安。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M].耿升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11]李克郁。土族《蒙古尔》源流考[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42-43.
[14]王国明。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12-13.
[15]马光星。土族格萨尔故事述评[A].格萨尔学集成(第 2 卷)[C].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928.
[17]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M].北京:中华书局,2009.237.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