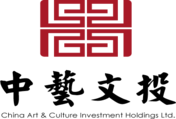佛教神足通及其对中古文学艺术的影响
2016-05-17 20:43:54 作者:何剑平 来源:《宗风》 已浏览次
一、汉文佛经小的神足通
神足通,又作如意足通、变神足、神境智通、神境智证通、身通。乃属佛教五通之一,六神通之一,神通原是印度的一般信仰,后来在佛法中渐渐流行,并被视为诸佛菩萨用作度众的方便法门之一[3]。在习惯于神教意识的一般信众中,由于对佛存有神奇的想法[4],故神通也一直被视为一种神奇变化的法术。一般而言,神通有六种,称马“六神通”,即:神足通、天耳通、知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漏尽通[5]。就化他而言,唯言神足通、天耳通、知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称为五通;就自证而言,则加言漏尽通,称六通[6]。有关六神通的具体释义,我们依据《长阿含经》第十七卷的异译本——东晋沙门竺昙无兰译《佛说寂志果经》——的相关描述得知:
1、神足通:以一身化无数身,无数身还令为一。独立现变,若干之慧。出彻墙壁,而无碍迹。譬如飞鸟游于虚空,出无间,入无孔,入地无挂,如出入水。经行水上,譬如履地。在虚空中,正跏跌坐,如飞鸟云。于是日月威神广远,以手捉持,而扪摸之。变身上至第九梵天。
2、天耳通:耳能彻听,闻诸天人所语,及蚊行喘息人物之声。
3、天眼通:心无所着,眼能彻视众生的业色,见天上天下善恶所趣。知道来生是生天或落恶趣等。
4、知他心通:普彻知他人心所念善恶是非,普及一切世间形类。
5、宿命通:见过去无数世事。见一世、十世、百世、千世、万世、千万世、无数世,往来周旋。
6、漏尽通:诸漏已尽。知烦恼的解脱情形,知烦恼已否彻底断尽:[7]。
在六通中,神足通最具非凡奇特的力量,是佛与圣弟子在定慧修证中一种超自然的神通,它能上天人地,能“出无间,人无孔”,自在无碍,这种神奇的力量给予人无限想象的空间。由此而在印度本土流传甚广,并在佛教典籍中获得极富文学性的记载。
从后汉到两晋之际,有关神足通的佛教经论相继被译成汉文。佛经方面,例如后汉安世高所译《佛说阿难同学经》——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四认为抄自《阿含》——记掘多比丘于般涅盘前,施演“或化一身,马若干身,或化若干身,为一身”等神足通;在表现佛陀传记的《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记佛得神通时“身能飞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亿万无数,复合为一”、“眼能彻视,耳能洞听”、“能彻入地,石壁皆过”之事;《普曜经》卷八亦记佛陀本人尝开化优为迦叶与五百弟子,令解道法,后者皆禀受经戒作沙门事。其中神足通乃佛陀为弟子施演教化之重要手段之一。这类关于诸佛菩萨六神通中之神足通的记载极多,不烦俱引。而在佛教论藏方面,印度早就出现了对神足通进行分类及解说的论着。这些经典亦在魏晋之际相继在中土得到传译。如代表着早期佛教的论藏和此后大乘佛教的论藏——《阿毗昙甘露味论》卷下、《十住毗婆沙论》卷十、《大智度论》卷五——均对神足通作了细致分类解说。例如《大智度论》卷五谈到“漏尽通”之外的前五通时说:
如意、天眼、天耳、他心智、 自识宿命。云何如意?如意有三种:能到、转变、圣如意。能到有四种:一者身能飞行,如鸟无碍;二者移远令近,不往而到;三者此没彼出;四者一念能至。转变者,大能作小,小能作大,一能作多,多能作一,种种诸物皆能转变。外道辈转变极久,不过七日。诸佛及弟子转变自在,无有久近。圣如意者,外六尘中,不可爱不净物,能观令净。可爱净物,能观令不净,是圣如意法,唯佛独有。
引文中提到的五通是:如意、天眼、天耳、他心智、自识宿命。其中“如意”即前述神足通。不同的是,《大智度论》将如意分为三种:能到、转变、圣如意。“能到”又细分为“身能飞行”、“移远令近”、“此没彼出”、“一念能至”四种表现形式,并认为佛及弟子在神足通方面的能力优胜于外道。这种对神足通的条分缕述,显示出早期佛教经论对佛说神通观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理论储备,同时亦可以看出神足通在文学上的重要性开始突显。相同的论述还见于另外两部早期论藏——曹魏代译失三藏名的《阿昆昙甘露味论》卷下及东晋太元十六年(391)由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译、被庐山慧远称为“出《四阿含》”[8]的《三法度论》卷上。
北凉年间,代表大乘学说的《瑜伽论本地分中菩萨地》的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极大丰富了佛教有关六神通的学说。据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及同书卷九《菩萨善戒菩萨地持二经记》,当时即有两本佛经“明义相类,根本似是一经”,它们是《菩萨地持》八卷和《菩萨善戒》十卷。前者由昙无谶译于北凉玄始七年(418)十月初一日(晋安帝世),后者则由求那跋摩译于宋文帝元嘉八年(431)之后。据《大唐内典录》卷五、《开元释教录》卷八,玄奘法师又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十五日翻译了相关内容,这就是加载《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七的《本地分中菩萨地第十五初持瑜伽处威力品》。据上可知,《瑜伽论本地分中菩萨地》在历史上至少有三个汉译本。然而引发我们兴趣的不是这三个译本的翻译情况,而是它们分别都谈到了诸佛菩萨六神通之内容,其中对六通中之神足通理论的发展尤为巨大,主要表现在对此前变神足的分类加以细说与布衍,使之更有系统。例如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卷二《方便处力品》谈到诸佛菩萨之力,略说有三种力,细分则有五种力,即神通力,法力,俱生力,共一切声闻、缘觉力,不共力。神通力位居五种力之首。神通即所谓六通:神足、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作证。神足略说有二种:一为变神足,二为化神足。其中前者,又名转变神足,累计共十六变神足,经文列出他们的具体内容:
1、震动,谓佛菩萨得自在三昧,能震动一切世界。
2、炽然,即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是等等。
3、充满,身放光明,充满一舍,乃至充满无量无数三千大干世界,
4、示现,谓诸佛菩萨安坐去来,下至恶道,上至人天,能现为一切沙门众等。
5、转作异分,或转变地为水,转变草木、泥土为饮食、衣服、璎珞、香华等诸庄严具,乃至转变沙砾瓦石为众宝等。
6、来去,石壁无碍,上至梵世,乃至色究竟天,若来若去,悉得自在。
7、大小,变小为大,变大为小(能令雪山如一微尘,令一微尘如雪山王)。
8、色像人身,能将一切大众,若村、若城、草木丛林及诸山地,一切色像悉纳于己身之中。时诸大众,各各自见人菩萨身。
9、所往相似,随其所至之处,能现形同一切众生:色像、身量修短、音声语言,悉与彼同。
10、隐显,于大众之前,百干度显现自身,然后隐没,隐没之后又复显现。
11、自在,菩萨能令众生若来若去,若住若语。一切随心。
12、障他神通,如来神力能障蔽控制他人所现之神力。
13、与辩,无辩众生,能给与辩才。
14、与念,于法失念,能令忆念。
15、与乐,无乐众生能与其乐。
16、放大光明,谓佛菩萨神力放光,遍至十方无量世界。
对于变神足的这些描写,重于文学趣味,反映了佛法通俗化的趋向。至于化神足,略说有三种:化身(化为一切众生形类)、化声(化为种种音声语言)、化境界(化为一切饮食等事),是名化神足。如此,诸佛菩萨具二种神足通。这种对神足通功能进一步的想象和繁富的分类,表现了历代说法者对神足通这种施教手段的推崇,不难想象,这种推崇是因为神足通本身所具有的神奇引发了信众浓厚的兴趣,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皈依佛教。
在宋罽宾三藏求那跋摩译《菩萨善戒经》卷二《菩萨地不可思议品》也有对变神足大致相同的分类。
逮至唐代,玄奘法师所译《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七之《本地分中菩萨地第十五初持瑜伽处威力品》可谓对诸佛菩萨神通威力最完整的论述。此品认为诸佛菩萨神通威力,即所谓六神通:一者神境智作证通,二者随念宿住智作证通,三者天耳智作证通,四者见死生智作证通,五者知心差别智作证通,六者漏尽智作证通,是名神通威力。不难看出,玄奘对神通威力(六通)的译法略同于昙无谶本。对于佛菩萨六通之一的“神境智作证通”(即旧译变神足),玄奘译本谓略有二种:一者能变通,二者能化通。凡此皆同于上述译本,所不同的是,对于“神境智作证通”种种品类差别之叙述较之旧译更为完整,认为佛菩萨神境智通中之能变神境智通有十八变(此不同于旧译之十六变或十三变),此十八变为:一振动,二炽然,三流布,四示现,五转变,六往来,七卷,八舒,九众像人身,十同类往趣,十一显,十二隐,十三所作自在,十四制他神通,十五能施辩才,十六能施忆念,十七能施安乐,十八放大光明。如是等类,皆名能变神境智通。通过比对旧译,尤其是昙无谶译本,可以看到,玄奘译本所译能变神境智通之十八变,实乃十六变。引起的差别仅仅在于玄奘法师将昙本中变神足中之第七种“大小”分译作“卷”、“舒”二项,而将变神足中之第十种“隐显”分作“隐”、“显”二项,如此才形成了后来较马通行的十八变,这无疑使得大乘经典中对有关神足通的描写在种类、内容上更加丰富神奇。此后我们看到,在印度,有关十八变的神通理论在《摄大乘论本》卷下、《摄大乘论释论》卷八、《摄大乘论释》卷八等论着中被重复征引。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从汉末佛教传人中土以来,作为六通之一的神足通概念,在印度佛教发展史和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均经历了一个丰富、发展的过程。早期汉文佛经对神足通的载述多零散无序,原始论藏及早期大乘论藏开始对之进行简单的三分类,北凉和刘宋至唐玄奘先后译出的《瑜伽论本地分中菩萨地》,在印度属龙树、提婆之后“全面组织大乘学说新出的文献”[9],其中对神足通作了详细分类整理,有十六变及十八变之说,神足通的理论一步步走向丰富和完善。
二、神足通在中土的传达和容受
早在汉代中期,由于西方文化的东渐,一些和神通相关的幻术或魔术已由西域传人中土,佛教六神通之神足通理论也随即输入,并在当时的士人中传布开来。现存文献保存了当时中国人对佛教的最初认识。如《牟子理惑》将佛的“恍惚变化”描写为“分身散体”、“能小能大”、“能隐能彰”、“欲行则飞”等,足证牟子对佛教神通的了解。同时亦说明东汉末年,有着崇信方术传统的中国人在初次接纳佛教时,其关注的重点首先是佛教的神通性。这或许是传教僧侣有意采用的教化方式所致。因为通过神足通之观念行化较易使人们接受和理解佛教,并以之拟比神仙方术。孙绰《游天台山赋》说:“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蹑虚。骋神变之挥霍,忽出有而人无。”此将道教之神仙王乔与佛教之阿罗汉升空蹑虚之形象并置,反映了时人心目中对神通的一种认识。
佛教神通观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得到广泛流传,在不同的社会层面有不同的接受方式。这一点,集中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神通作为起信化俗之技能而受到一些奇异僧人的推崇。神通观传入中土后,始先亦是作为开导蒙俗之手段。对于当时不识佛法、不达深理的中土民众而言,神通乃起信之最佳工具。竺道生《妙法莲花经疏》释《见宝塔品》所谓“人情昧理,不能不以神奇致信”,凝然《维摩经疏庵罗记》卷第二十六所谓:“神变示导,众生见之起信。然后方有教诫示导,记心示导故。”又说“现神境通令物生信”,都谈到神通行化在起信方面的重要位次。鉴于神通在教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以神通法术而着称的奇异僧人在南北两地层出不穷。《高僧传》、《续高僧传》两书“神异”、“感通”篇记载了魏晋至南北朝许多有关神通的事例,其中相当部分发生在此一时期。当时善于神通术的僧人有佛图澄、单道开、犍陀勒、诃罗竭、竺法慧、安慧则、史宗、释昙始、法朗、邵硕、慧安、保志等。需指出的是,他们并非夸街方伎,而是以权宜方便达到“反常合道”[10]之目的。例如魏晋以来,北方战乱频仍,在“郡国分崩、民遭屠炭”之际,藉神通术以止杀戮,成为佛图澄济拔危殆之教化方式。其后佛调、耆域、涉公、杯度等,亦相次以神通化俗,显现神奇,其灵迹怪诡之传说事迹盛传于中国民间。
二、在当时注重实践禅修的僧侣阶层,神通则一直被视骂修行禅定而获得的不可思议之力。在他们那裹实践了佛教神通与僧俗修习禅定的结合。慧远问鸠摩罗什念佛三昧义,什答云有三种,其中由修定而得的神通——“菩萨或得天眼、天耳,或飞到十方佛所,见佛难问,断诸疑网”——为见佛三昧之一种[11],陆澄《法论目录》第八帙《定藏集》着录慧远《释神足》一文,观题可知是从禅观角度对六通中之神足通的阐释。慧皎《高僧传·习禅论》论及禅与神通之关系:“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稣。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隋天台智者《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十及《法界次第初门》卷中所言六神通,其重点则在说明观禅功用之法,如前者说“若欲为化众生,现希有事,令心清净,应当广修一切神通道力。所谓六通,……十八变化等诸大功德,皆应住此背舍胜处一切处中学。既学得已,令多众生睹见欢喜,信伏得度,故修神变”,都在说明广修神通道力为行化之要术以及深修禅定可得五神通的道理。
三、佛教神通也引起上流社会的兴趣,并作为参玄问难的话题进入知识阶层的论议。魏晋玄学的兴起,由于论辩风尚的持续不坠,佛教论议逐渐与清谈风尚相结合,有关变神足或神通的义学论题也渐次进入南方上层士大夫及僧人的视野,《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名士谢安、孙绰等所钦敬的义学僧人、本无异宗的代表竺法汰说“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耳”,谢灵运《山居赋》自注谓“寂漠虚速”之境“既非人迹所求,更待三明五通,然后可践履”云云,此处所说的“三明”,据刘孝标注,一日过去心之明,即宿命通。二日见在心之明,即天眼、天耳、身通、他心、漏尽通。三日未来心之明,即天眼通。凡此皆为当时知识阶层对此一议题进行过论难提供了某种证明。而在当时北方的后秦王朝,亦将神通作为问道参玄的话题,如《广弘明集》卷十八载姚嵩《谢后主姚兴珠像表》难姚兴《通圣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之义,在此所谓的“放大光明”义,实乃神足变十六或十八中之放大光明义项。又如《出三藏集记》卷八载释僧肇《维摩诘经序》之言曰:“《维摩诘不思议经》者,盖是穷微尽化、妙绝之称也。……至若借座灯王、请饭香土、手接大干、室包干像,不思议之迹也。”在此,僧肇所谓“借座灯王”、“手接大干”、“室包干像”等情节,乃见于《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所谓“请饭香土”情节,则见于《维摩诘所说经》·《香积佛品》。它们都是表现维摩诘诸种神足通的。然而,我们不难看出,僧肇对维摩诘神通的认识仍服务于他在教理上提出的本迹新说。总之,在这些例证中,神通带着魏晋以还佛教义学辩难析疑的色彩。既便当时以神异名世的僧侣中也多带有神异与义理兼备的特征,如《高僧传》载竺佛图澄“妙解深经,傍通世论”,“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合若符契,无能屈者”,史宗“应对机捷,无所拘滞,博达稽古,辩说玄儒”,保志“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皆是。
四、神足通作为一种异术方技被融入道教或民间巫觋的宗教修习实践之中。在当时崇信方术的中土,佛教神通(主要是神足通)的某些要素也为早期道教或普通民众所吸收借用,从而成为道教和各种地方性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在传统和外来这两种文化的互动过程中,祝巫或道教信徒可谓较早接受和利用了佛教神通观念,完成了神仙方术和佛教神通两种不同神性特征的融合杂糅。例如《太平御览》七百三十五引《幽明录》说:东晋太元中,临海有李巫,“能卜相,作水符,治病多愈,亦礼佛读经”;《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引《幽明录》说:吴兴乌程人陈相子“始见佛家经,遂学升霞之术”等,都可谓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例证。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佛教神通观除了上述表现外,还以幻术的形式在信众和非信众中广泛传播。关于神通威力的记载越来越多地见于南北朝子部类,史部地理类等典籍中。例如:
(一)《列子·周穆王篇》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人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核。千变万化,不可穷极”。
(二)《抱朴子内篇·对俗》谓九百多种按行有效的“幻化之事”:“吞刀吐火,坐在立亡,……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玉为饴,溃金为浆,人渊不沾,蹴刃不伤”。又同书《道意》论及张角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事。
(三)刘义庆《幽明录》记东晋安城之俗巫安开“善于幻术,每至祠神时,击鼓,宰三牲,积薪然火盛炽,束带人火中。章纸烧尽,而开形体衣服犹如初”。
(四)《晋书·夏统传》记载说:夏统母疾,统侍医药,“其从父敬宁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陈珠二人,……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
(五)《西京杂记》卷三记有东海人黄公,善为幻术,能“立兴云雾,坐成山河”。
(六)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论及当世“祝师及诸幻术”能“履火蹈刃,种瓜移井,倏忽之间,十变五化”事。
(七)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一记景乐寺中之“异端奇术”:“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
(八)《洞真上清神州七转七变撰天经》曰:飞神州七变怜天经》第一之变,当先化身为云……第二之变,当化身为光……第三之变,当先使其身化为火精……第四之变,与气浮沉,炼身化水……第五之变,当化身为龙……。”
(九)《隋书·五行志》载: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出世”。
以上九例说明,佛教神通观已深人人心,尤其是六通中之神足通以故事或幻术等形式在中土赢得大批信众,并具有技艺化的特征。第一例中的“西极化人”一语,当受化神足之化身、化声、化境界之启发而致。例二和例八则反映了道教方术对佛教神通的吸收。据陶弘景《真诰·甄命授第一》,“仙道有七变神法七转之经”,当即指例八之《洞真上清神州七转七变伤天经》,“七变”为变化分形之法。三、四、九三例,反映了神通幻术和民间宗教礼仪或运动之间的联系。例三和例四表明神通幻术被携人巫觋们所举行的民间宗教仪式之中。
在魏晋动乱中,中国士族为避战火,曾相次迁徙朝鲜、日本,佛教神通亦随之东传。例如西晋崩离后,不少汉人从中国东北、山东地区辗转来到朝鲜半岛,司马氏一族无疑属于此一时期新迁入的士族[12],始先广泛分布于高句丽至百济,盖在五世纪初期相次移至日本,其日本氏姓为“鞍作村主”一族,他们不仅成为最早的佛教传播者,而且也将佛教神通从朝鲜半岛带到日本。如《日本书纪》、《扶桑略记》均载皇极天皇四年,“高丽学问僧等言:同学鞍作得志,以虎为友,学取其术。或使枯山变为青山,或使黄地变为白水,种令奇术,不可殚究”之事[13]。
至隋代,进人了对神通观的总结时期,出现了净影寺慧速有关变神足的总结性论着。慧速依前所译大乘经论,对佛教神通观念进行了梳理和解说。其《大乘义章》卷二十(本)专立“六通义九门分别”,在第九门“依经辨相”条,对神通(或名身通、或名神足)义顼进行传述和阐释。慧远认为,身通(神足)有二种:一变,二化。改换旧质,名之为变。无事不现,说以为化。是变多种,要为十六。显然,慧远解说的佛经依据是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此种对佛教神通观的整理解说可视为隋前最完整的义学阐释。我们注意到,慧远将神足类别特征之一的“变”,极形象地定义为“改换旧质”,这是前人未曾论及的。此后吉藏、窥基等对神足变的定义皆承此说。
逮至唐代,随着玄奘《瑜伽师地论》等大乘经论的传译,有关佛教神足十八变的理论日益引起中土僧侣阶层的崇重,并在载籍中得到大量引述。在此一时期,对神足通理论的接受又出现了新的景观。
首先是开始用变神足理论分析佛教文学的典范作品(具有文学特性的佛教经文之情节)。这一点,在中土僧俗有关佛经的注疏中有较突出的反映。典型的是窥基对被称为佛教文学典范的《维摩诘经》的注疏本——《说无垢称经疏入在此疏中,窥基在“经起所因门之四”谈到如来威德之大,指出此经显示了佛及维摩诘的神通威力。并认为《维摩诘经》中的一些故事场景呈现了圣者的十八种神变(此十八种变属如来六神通之中的神境智作证通,即前述神足通)。《维摩诘经》共十四品,表现佛及维摩诘神通变化的情节主要集中在《序品(佛国品)》、《文殊师利问疾品》、《不思议品》、《观众生品》及《香积佛品》。在《说无垢称经疏》卷一,窥基采用玄奘译本所提及的神足通十八变理论对上述品目中故事情节进行归类和解说。认为《维摩诘经》中有些神变的表现形式具有兼容性,如《序品》中之宝积献盖情节既可归于十八变中之第五“转变”,亦可归属十八变中之第八“舒”;《不思议品》中的灯王遣座既属十八变中之第六“往来”,亦属第十三之“所作自在”。《观有情品》中之“此室常现一切佛土功德庄严”,既是转变,亦属众像人身。在中土佛教史上,用神足通十八变理论对佛教文学作品进行解说尚属首次。
窥基之后,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十二、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二、《止观辅行传弘决》卷十、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五十六、《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六十一、卷八十五均在释经中引述了神足通中十八变的内容。而由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二及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八十五可知,十八变的内容在唐代还被编成了偈颂。
其二是对神足通的阐释呈现中国化的倾向。这一点在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六对变神足的诠解有较马突出的表现。其观点可概述如下:一是神变与变神足同:“神境智作证通名神,有威势名力,亦神亦力,即名神变,记义如前。”二是变相之概念源自佛教神通概念;三是对神变的诠解增添了不同于其本意的新质内容。如对“能变”的解说谓“能变谓转换旧质”,对神变的解说谓“作用难测,名之为神。转易不定,称之为变”,后者释“神”,明显化用了《周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语义。类似的解说还见于窥基《说无垢称经》卷第二本:“妙用难测名神,转换旧形名变”。窥基关于“神变”的这种解说,显然与慧远关于神足类别特征之一“变”的观点一脉相承。此外,唐代诗人王维在《给事中窦绍为亡弟故驸马都尉于孝义寺浮图画西方阿弥陀变赞并序》中引用《易经·系辞上》“游魂为变”,将变与轮回过程中的变化相联系[14]。王维的解释,与变神足所具有的佛教色彩的神变之本意,渐行疏离。
在这一时期,因受变神足观念的影响还出现了众多为普及佛教、弘扬神通信仰而编撰的论着。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数种:
(一)释道宣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夏六月二十日,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三卷,载录神僧圣寺事迹,又于高宗干封二年(667)仲春撰成《律相感通传》。并作《续高僧传》,立《感通》篇。这些论着都在某些方面彰显了神通威力。其《释迦方志》卷上记“昔有二贫人,各施一金钱,共画一像,请现神变。像即现,胸以上分为两,身下合为一”,又《释迦谱》提及用魔法变出一棵树的故事,并说“此变乃是劳度差作”,反映出神变和神变艺术的结合。
(二)释道世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三月三十日完成释家类书《法苑珠林》一百卷的纂集,于本书卷二十八设《神异篇》,卷三十二设《变化篇》,其中后者有三部:述意部、通变部、厌欲部。在述意部云“所以放大光明、现诸神变者,此应十方诸大菩萨将绍尊位者耳”,又厌欲部末颂曰:“大圣神变,随事启蒙。服以邪道,化现神通。”凡此皆表明:其“变化”之名义实乃神通或神变。又道世在《变化篇》三部中皆引述佛经中神变故事,又在最后附以中土表现神异事件的“感应缘”故事二十五例——这些故事采自《搜神记》、《异苑》、《幽明录》、《齐谐记》、《述异记》、《续搜神记》、《洛阳寺记》等——被称为“能变”或“变”,首次将中土感应缘与印度变化故事并置编排。其称之为“能变”,显然是直接因袭玄奘译本中六通之一的“神境智作证通”(即旧译变神足)中的“能变通”观念。
(三)高宗永隆二年(681)辛巳,沙门释复礼,因太子文学权无二,述释典稽疑十条,用以问礼,请令释滞。礼遂为答之,撰成二卷,名曰《十门辩惑论》。我们注意到,在这部“宾主酬答,剖析稽疑”的佛教论着裹,释复礼将《通力上感门》列为“十门辩惑”之第一门,并在此一门中大谈维摩诘“掌运如来”之神力及其缘由[15],可见其对神足通之倚重。
(四)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论》言及“佛道神化”之事,云天竺国“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又云佛法有“好大不经,奇谲无已”的神通特质。对此诸句,唐代李贤等皆征引《维摩诘所说经》之《不思议品》与《佛国品》表现维摩诘及佛陀神力的经文以注释之。
这些记载多盛赞圣者的神通威力,无疑暗示了佛教信仰通俗化的一种转向。它表明,在唐代初年,中国僧俗开始关注神足通道一佛教观念所具有的宗教意义:一是“引诸众生人佛圣教”,二是“惠施无量受苦众生”[16]。当然,以上这些论着的产生也与唐高宗、武后朝对神通的崇重有关。正如唐人刘肃所言:“及高宗崩,四方多说怪妄,以为祥瑞。”[17]武后、中宗成为这种风气的肇端者。由于对佛教符谶的重视,武后对能知未来的僧人、道士特为信重。据《宋高僧传》,自高宗末,武后时常诏万回人内道场,赐锦绣衣裳,宫人供养。据《朝野贪载》,大足中,有袄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书厌,则天于内安置。道土罗公远因“有异见,言事皆中”,则天“敕追人京”。中宗神龙二年,敕万回禅师赐号法云公圆通大士,三年,敕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大师,师既至,尊为国师,出居荐福寺,帝及百僚皆称弟子。及其以景龙四年三月二日减度后,“孝和皇帝申弟子礼,悼大师之情”[18];玄宗开元三年,诏一行禅师入见,帝咨以安国抚民之道,及出世法要,称为天师,一行预知帝有当归之谶。天宝中,法津禅师因为“悬鉴来事,见重时君”,[19]。凡此表明:自高宗朝后直至玄宗朝,均对具神通道力的僧人特加礼数。对符瑞谶语的趣好成为时尚,波及社会各阶层,在这种社会风尚下,僧侣术士,皆以神通术取悦人主,佛教的方伎化或道教的神通化成为遣一时期统治者趣尚之所在。能拯拔现实疾苦、息灾增益、对人事具有睹微知幽之神力的僧人,重新受到民众的归信和尊宠。其事迹日趋神化,被称为“神僧”或“圣僧”[20],不仅如此,在唐代,其追随者的故事也被神化[21]。表现之一是:有奇术之人的故事在社会上盛传[22],如万回一日往返万里,僧一行之门水西流,不空与罗公速同祈雨互较功力、泗上僧伽,十九类身之应现等反映僧侣神通的怪异之事亦大传众口[23]。其中万回被视为获得如意通(神境智作证通)的人物[24],开元二十五年五月,徐彦伯撰《唐万回神迹记》(《金石录》卷六),伯3490《供养题记》载天成中归义军节度押衙李神好“敬绘万回大师”,愿其“垂悲圣力,救护苍生”。可见,利用神变来使异教徒皈依佛法之方式,无疑在中国民间佛教传统中源速流长。
三、神足通对中园文学艺术的影响
佛教神通中之神足通以其好大不经、诡异莫测的表现形式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至深影响。此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一种文学观念,成为南北朝众多文学家编撰志怪故事和韵文所凭据的重要法宝;其二是作为一种教化方式,神通被运用于讲唱伎艺,直接导致了通俗艺术作品——变文、变相、转变的产生和发展。
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载录了前一方面的内容。如魏晋之际输人中土的佛教神通观成为葛洪《神仙传》中左慈等方士变化之术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对中古志怪小说表现神通情节和神通道人起到示范作用[25]。《神仙传》的文本在晋宋之际颇行于世,此后转相仿效,蔚成风气。如《拾遗记》载燕昭王七年身毒国道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变为婴儿,倏忽而死”事,《搜神记》载庐江人左慈,“移逮令近”而得到吴淞江鲈鱼及蜀中生姜,又言曹公令人捕之于市,出现“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谁是”之局面,同书同卷载介琰能变化隐形,吴主“敕缚琰,着甲士引弩射之。弩发,而绳缚犹存,不知琰之所之”云云,介琰乃用变神通中之“隐显”之法。《灵鬼志》记“外国道人”寄担人笼中,“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事,齐朝祖冲之《述异记》载黄衣人“径上崖,直人石中”之神异,北齐王琰《冥祥记》所记晋沙门佛调的分身之术、晋犍陀勒的示现神足等。这意味着,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家在结撰故事时明显受到佛教神通观念尤其是六通中变神通的启示和影响,职是之故,神通道人亦大量出现在中土的志怪小说之中。由前面的论述可知,左慈故事,表现的实际是变神通(移远令近、同类往趣)之故技,介琰乃用变神通中之“隐显”之法。
作为演唱之用的道教文学样式的玄歌亦保存了“变神足”影响的痕迹。伯2004《老子化胡经玄歌卷第十》载有《老子十六变词》十八首,这些诗歌出现的时代已被证明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毁法之后[26],属北魏人附丽而成。《老子十六变词》依据《易》的九宫八卦方位的变更来组织场景转换,然更为明显的是,十六变词在诗中不断重复的老君“变形易体”之神力以及十六变之名义当受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卷二所言十六种“转变神足”的启示。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载黄公幻术,又载淮南王好方士事,言“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乌寒暑,喷嗽为雨雾”之变化之术。《太平广记》卷五十六引《集仙录》载大禹理水,诣云华夫人处,睹其“隐见变化”:“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这同时表明,佛教神通观的传播还得力于道教文化对它的积极融摄。事实上,自汉末魏晋以来,道教徒已形成借用佛教现成教规、教理以证成其说的风气,如葛洪于《抱朴子内篇·祛惑》中借用佛经中关于音乐树的描写来增华道教神山昆仑的情状[27],陶弘景《真诰·甄命授第二》对东汉佛经《四十二章经》的模仿[28]等,皆为显证。
在艺术形式方面,变神足在唐代文学艺术中有着持续不断的流传:
(一)转变。转变是一种看图讲故事的艺术形式,由前文所论可知,其名义当来自神足通十八变中第五转变。原本应是源于佛教性的演艺,传入中土后,表演者或为僧人,或由世俗艺人组成。转变艺术在当时颇具吸引力,渗入到唐代社会各个文化层面。据唐郭浞《高力士外传》、《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九“宋昱韦儇”条,我们知道,转变的表演场所变换不定,既可在皇帝面前演出,亦可在通衢大道上层演,唐代还有定期转变的地方性场所,在白居易、张枯的时代,九世纪初变文故事已相当成型,可供引述。或在此之前,转变艺术已在中国许多城市流传。颇有文化修养的诗人们都精熟和了解变文的内容,并自如用作玩笑的素材[29]。这都说明其对上流社会人们的吸引力和效用。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才调集》卷八)和李速《转变人》[30]都为此提供了例证。如前者即告诉我们有关转变艺术一些零星的信息:(1)蜀女是来自四川的女艺人;(2)转变中可利用画卷;(3)转变具有世俗性的题材;(4)所描述的虽是一种口头转变,但它是画面变文的前驱;(5)由收录该诗的韦毅所编《才调集》的情况推测,此诗可能作于中晚唐;(6)鉴于敦煌变文中有《昭君变》,此诗也引起了口头转变和画面变文(书面文字的转变)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31]。可以想象,专讲转变故事的艺人曾活跃于整个中国。
(二)变文。“变文”和“变”是两个同义且可以互换的名词。作为唐五代敦煌地区丰富多彩的通俗宗教文学体裁之一,变文是佛教进入中土以后形成的一种表现神变故事的佛教文学体裁和文字记录。和讲经文不同的是,变文起初被用于讲唱佛经中的神变故事,如佛本生、本行.、因缘果报故事中的神变情节等,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世俗化和中国化,变文亦逐渐被用以讲述非佛教的故事。敦煌写本今存21种变文作品,采用世俗题材者居多,其内容涉及王陵、舜、李陵、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和张义潮、张淮深等现实人物[32]。引人注意的是,这些有“变”或“变文”标题的文书在叙事情节上都还保留着神足变本意的痕迹。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对个别作品的考查来证明这种解释。以非佛教的题材而言,如《舜子变》记瞽叟毒打舜子,上界帝释“化一老人,便往下界来至,方便与舜,犹如不打相似”事;记瞽叟等埋井,欲填压舜,“帝释变作一黄龙,引舜通穴往东家井出”事;又记父子相识,舜“拭其父泪,与舌舐之,两目即明”等事;《汉将王陵变》记刘邦下诏祭王陵之母,“陵母从楚营内,乘一朵黑云,空中惭谢”事,《前汉刘家太子传》(后题《刘家太子变》),记童子遇在街坊,监官遣打布鼓三声,致使“天地昏暗,都无所见”等事:在讲述奇迹事件中显示出超自然力。与其说故事情节充满了神奇的事迹,勿宁说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代表着人神超自然神力的变神足的传统。
(三)变相。是一种佛教题材并具复杂绘画形式的绘画,就质地而言,它有诸种艺术表现形式:立体的彩画、小型微雕的“杂变像”、以铜摹制的浮雕、堂殿壁上的图画、卷轴画、织品等[33],我们认为此类作品之被称为变相,乃在于它们原本皆以表现佛教神变内容为主,其变之名义源自佛教变神足观念。由于受到六朝以来造像风气的影响,随着佛教尤其是净土信仰的普及,变相艺术在唐代极为兴盛。张彦速《历代名画记》卷三记录了见于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各种题材的变相作品。初唐净土宗大师善导曾“写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三百铺所”,致使出现“满长安城中并从其画”的盛观[34],刘秀《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全唐文》卷二七八)所记西北地区的变相场景:“于堂中面画净土变,面西化地狱画、高僧变,并刊传赞……于南禅院回廊画付法藏罗汉圣僧变、摩腾法东来变、七女变。”王维《西方变画赞并序入李白《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并序》、任华《西方变画赞》、梁肃《壁画二像赞并序》、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五《怪术》载有术士因寺中大斋会献伎“方饮水,再三噀壁上,成维摩问疾变相”之事,同书同卷《寺塔记》又载有元和末年俗讲僧文淑装修“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壁面之事:均表现了各种佛教题材的变相艺术形式在中土南北佛寺、斋会等宗教活动场所的流行盛况。
(四)散乐杂戏。自佛教西来,除变文、变相外,变神足观念还渗入中土其他艺术领域——歌舞杂戏。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王棨《吞刀吐火赋》(《文苑英华》卷八二)言及奇幻玄妙的吞刀吐火之术:“原夫自天竺来,时当西京暇日,骋不测之神变,有非常之妙术”。从《隋书·音乐志》及《旧唐书·音乐志》可见这些散乐杂戏中受变神足影响的艺术内容: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隋炀帝于东都盛陈四方散乐,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见“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又有神鳘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汉天子临轩设散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化成黄龙,修八丈,出水游戏,辉耀日光。绳系两柱,相去数丈,二倡女对舞绳上,切肩而不倾。如是杂变,总名百戏”。其中场景的更迭变动,极富视觉刺激效果。
以上记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源于魏晋南北朝以还汉译佛经的变神足观念在唐代民众佛教的背景下有着生生不息的传承。其突出表现是:当佛教义学在唐代衰微后,民间佛教传统中却出现了对神变艺术津津乐道的高潮。阕于这一点,可以再举出一个典型例证,即维摩诘变相在唐代中后期的变化。早在魏晋以还,中国人即认识到“大设灵奇、示以报应”的作法乃佛教之根本要素之一,“以神奇为化则其教易行”[35]的思想成为佛教在民间传播的动力,并巧妙契合了自史迁以来中国文学“广异闻而表奇事”[36]的写作传统。《维摩诘经》自《佛国品》至《问疾品》,为中土上层信仰者塑造了一个辩才无碍的居士形象,《问疾品》以下品目则为信仰者塑造了一个具有不可思议神通力的信仰对象。其中崇尚神通成为维摩诘信仰在民间广泛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贺世哲主编《敦煌石窟全集》第7册《法华经画卷》所附《敦煌石窟维摩诘经变各晶统计表》,中晚唐,显示佛及维摩诘神通力的品目重新受到崇信。实际上,这意味着神怪故事内容在维摩经变中的增长。例如在维摩诘经变中表现佛之神变的有《佛国品》中的宝盖供养、净土之变等。在中晚唐的维摩诘经变中,反复出现的正是关于这些神变的画面,而每一个表现神变的画面在原经中都是一个吸引听众的故事,同时义学僧对于维摩诘教理的讲说,亦出现对神通的偏好,如斯4341号敦煌写卷有讲经和尚讲论《维摩诘经》中之六神通义等。其中有些神变画面,我们还可以在《维摩诘经讲经文》中找到相应的情节。如斯4571号、俄藏Ф101号(《维摩碎金》)、斯3872号等三本《维摩诘经讲经文》,均演绎了本经《佛国品》的部分内容。总之,维摩诘经变在中晚唐的特点是表现维摩辩才难敌、张扬其智慧殊胜的画面减少,而《问疾品》以下广明维摩诘神变自在、显示其神通殊胜的画面增加,反映出信仰和神变艺术的结合。同样可以作为例证的还有以下作品:
(一)《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介绍“杂手艺”的各种巧名目时提及“变线儿”。这里的“变”似指一种杂耍或戏法。此完全可看作印度的说书艺术兼魔术在宋元的遗存[37]。
(二)《西游记》第二回悟空战混世魔王,“拔一把毫毛,丢在口中嚼碎,望空喷去,叫一声‘变!’,即变做三二百个小猴,周围攒簇”:显示出后世的民间佛教对于神足通的偏爱和承继。
(三)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一载王生求崂山道士授穿墙之术的故事情节,乃源于佛教表现穿越墙壁能力的神足变通。
这些作品表明:在唐代以后,神足通“神变无量、转易多端”[38]的诸种表现形式已成为中国艺术家结撰故事常用的手法。利用神足通营造虚幻神奇的空间,使人们离开凡庸常规的人生场景,极大满足了好奇心和幻想力,并激发了人对宗教的信心,这一手法在后世民间佛教文学的传统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1]教育部人丈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840007]。
[2]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佛教信仰、佛教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
[3]《大智度论》卷三十四,《大正藏》25:313a,即《大正藏》卷25,313页上栏,下同。
[4]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正闻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
[5]《佛说长阿含经》卷九,《大正藏》1:54b、58a。
[6];凝然:《维摩经疏庵罗记》卷二十六,《大日本佛敬全书》第5册,株式会杜名着普及会刊,第371页上。
[7]《大正藏》1:276b。
[8]释慧远;《三法度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正藏》25:20a。
[9]吕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第209页。
[10]《高僧传·神异论》。
[11]《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卷中,《大正藏》45:134b。
[12]韩升:“司马氏与中国佛教传播日本”,《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3]《扶桑略纪·帝王编年记》,《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十二卷,国史大系刊行会,昭和七年(1932)五月版51页。
[14]Victor H.Mair,T' ang Transformation Texts,chapter.3,pp.4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5]《大正藏》52:551b。
[16]窥基:《说无垢称经疏》卷一,《大正藏》38:996c。
[17]刘肃:《大唐新语》卷六《友悌》。
[18]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全唐文》卷二六三。
[19]王世平、朱捷元:“西安东郊新发现的唐法津墓志及塔铭”,《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1983年。
[20]《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一,载王昌龄《香积寺礼拜万回平等二圣僧塔》。
[21]《宋高僧传·元晓传》、《宋高僧传·万回传》、《宋高僧传·安静传附徐果师传》、《宋高僧传·阿足师传》。
[22]《酉阳杂俎》前集卷五《怪术》。
[23]《酉阳杂俎》前集卷三《贝编》。
[24]《宋高僧传·万回传》系辞。
[25]何剑平:“葛洪《神仙传》创作理论考源——以《左慈传》为考察中心”,《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6]敦煌遗书伯2004残卷,并见逢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253页。
[27]同注[25]。
[28]《朱子语颤》卷一百二十六:“道书中有《真诰》末后有《道授篇》却是窃《四十二章经》之意为之,非特此也。”
[29]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
[30]查屏球:《新补<全唐诗>102首一高丽“十抄诗”中所存唐人佚诗》,《丈史》总第六十二辑。
[31]Victor H.Mair,T' ang Transformation Texts,chapter.6,pp.15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2]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370页。
[33]巫鸿:《何为变相?》,《礼仪中的美术》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34]唐道铣:《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卍续藏经》第13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卍续藏经会编印,25页。
[35]释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一《王谧答桓玄应致敬难三首》,《大正藏》52:446c。
[36]《三国志》卷二十九《方技传》。
[37]梅维恒:《唐代变文(下)》,杨继东等译,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第185页。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