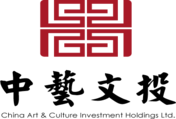论武昌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佛像的莲花座渊源
2016-05-07 23:32:26 作者:张同标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已浏览次
内容摘要:长江中下游的汉晋佛教造像中,极为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佛像的莲花座,这是与长江上游四川地区的汉晋佛像截然不同的一个特点。武昌莲溪寺的东吴永安五年(公元262年)纪年佛像,足踏莲台,莲茎左右各分出一根细枝,枝端有莲花。这是很可能中国纪年造像中出现的首例莲花座,而且是古印度“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的雏形。莲花座,在古印度首先出现于拉克希米和梵天造像,与佛教无关。直到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才与佛像造像发生联系,而且,仅限于“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由此出发,并参照中国古籍文献,可以判断,中国汉晋时期独立出现的莲花图像与佛教的关系无关,不能作为早期佛教传播的证据,当时与佛教有关的仅有长江中下游的莲花座一种。
关键词:武昌莲溪寺佛教造像;莲花座;莲花图像;舍卫城大神变造像
作者简介:张同标,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
二十多年前,阮荣春教授主持研究的“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首次向世人展示了长江沿线的汉晋佛教造像。阮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南方的长江沿线已发现有大批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并在同时期的日本古坟中也发现有十多件类似的佛像造像器物。从造像风格分析,主要是受中印度秣菟罗造像流派的影响所致。可以看出,东汉、西晋之间,从中印度经长江流域到日本,存在着一条早期佛教造像的南方传播系统。这些造像中有纪年的三十余例,多集中在公元320年以前,而当时的北方,最早的敦煌石窟尚未开凿,而且没有发现一例佛像作品,由此可以表明,佛教造像是先兴起于南方而后弘盛于北方的[1]。近年来发现的“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纪年佛像[2],把中国佛像出现的时间上推至东汉中期,也为编定印度佛教造像的早期历史框架提供了重要的编年座标。
长江中上游和中下游的汉晋佛教造像形成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大体来说,四川的佛像以摇钱树佛像为大宗,佛像多举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捏衣角。江浙一带的佛像,多禅定印,有莲花座,莲座两侧有双狮或龙虎的头部,与川地佛像明显不同。从中国文物以及古印度佛教造像发展史实来看,都是前者早后者晚的。由于长江中上游与中下游佛教造像的明显区别,缺乏明显的传承关系,难以视为同一造像系统,因而推测,这种情形,可能与两地佛教造像的不同的外来源头和各自输入途径有关,我们建议作为两个系统来考虑。长江上游应当考虑途经滇缅道与古印度的联系,后者更应该考虑途经南海、交趾等地与古印度联系的海上通道。
对于长江中下游的佛教造像来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武昌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公元262年)纪年墓中发现的鎏金铜带饰佛教造像。1959年发表的简报描述该佛像:“鎏金器物附件形似杏叶,表面刻画有佛像。”该墓还出土了“永安五年,丹阳石城校尉彭庐,年五十九居沙羡县界”铭文铅券[3]。这件长约5 cm衣带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制品,其制作年代可能比永安五年更早一些,粗略地把这件铜带饰确定为永安五年,大体是恰当的。这时,中国的第一位僧人朱士行出家(260)已经两年。自造像被报道以来,有许多研究者注意到这件造像。对造像是佛陀或是菩萨的尊格属性进行了讨论,或者对造像的域外渊源和传播途径进行推测。这件造像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纪年造像,虽然后来被延光四年摇钱树佛像所替代,但仍然是极少量的早期纪年造像之一,其价值是毋庸讳言的。
北京大学的宿白教授,曾指出这件莲溪寺造像,“肯定是佛像”,“这样的佛像与当时中原地区出现的形态、衣饰以及端正的坐式很不相同,却与印度支那南端金瓯角1—2世纪的奥高遗址所出的小铜佛有相似处。因此,我们估计它可能是从南海方面传来的型制”[4]。阮荣春教授把两个或多个地区同时输入佛教造像称之为“多中心波动式”[5],并对佛教造像海路传播和交趾佛教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我们认为,莲溪寺造像明显缺乏与四川早期佛像的联系,考虑到汉晋佛像可能存在着两种系统和多种传入可能性,理应重视与南方海路的关系。著名的康僧会就是从海路来到交趾,然后进入东吴境内的。他“以吴赤乌十年(248),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高僧传》卷一本传),其时略早于莲溪寺造像的铸造时期,也说明他“设像行道”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佛教信仰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史实,说明吴地造像与南方海路联系甚密。虽然武昌莲溪寺这种类型的佛像,中国仅知这一例,古印度和东南亚尚待进一步调查,但这尊佛像与南方交趾和海路入传有关,却是应该积极予以考虑的。
南方海路交趾道传入的佛教造像,与滇缅道传至四川的汉晋造像相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增加了佛像的莲花座。莲花座,是长江中下游汉晋佛教造像的重要特征。
莲溪寺造像可能是中国首次出现的带有莲花座的佛教造像,至少也是有明确纪年的首例。其他的魂瓶或铜镜上的佛像虽然也有莲花座,但其时代一般都晚于这件莲溪寺造像。截止于西晋末年魂瓶逐渐消失为止,长江中下游的莲花座佛像流行了50年左右的时间(公元262—313)。
本文对以往多被忽略的莲花座予以特别的关注,认为:在古印度,莲花座,首先与拉克希米和梵天两类印度教神像有关,后来被引入佛教,虽然始于三世纪中后期,但流行时期可能要晚至四世纪。与莲溪寺造像可能是经南海输入中国的,其原型应该是“舍卫城大神变造像系统”的雏形,大神变造像自五世纪起开始盛行,由莲溪寺造像可以证明其兴起时期应当早至三世纪。中国汉晋时期独立出现的莲花图像,与莲花座不同,既没有明确的佛教属性,其命名也多有望文生义之嫌,不能作为研究早期佛教的证据。
一、荷花与拉克希米的联系及其象征意义
本文建议莲花与莲花座分开来讨论,认为两者在中印两国的早期图像中不宜混为一谈。以后世的像例而言,无论莲花或是莲花座,都是佛教的象征,但早期造像则未必如此。古印度早期各类造像,我们发现:一、在印度教系统的造像中,较早出现的甘迦拉克希米(Gaja-Lakshmi),她站在莲花座上。其后出现的是梵天造像。二、观世音菩萨或者莲花手菩萨,手执长茎莲花,莲花从观音脚边长出,一直伸到肩部(由于目前难以确定早期造像的流行时间,姑且暂时搁置)。前者的两种印度教神像以莲花为座,而佛教的观音菩萨是手执莲花,两者并非一回事,所以本文把莲花与莲花座分开来讨论。前者出现的时间很早,后者出现时间并不很早,两者并非同时出现,所以,探讨莲花座与佛教造像的联系,也得把莲花与莲花座分开来讨论。
这里先专门讨论甘迦拉克希米(Gaja-Lakshmi),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古印度最初出现的带有莲花座的造像,第二、这也是最早被引入佛教用以装饰窣堵波的典型造像之一,第三、常有论者以为这是表示佛母摩耶夫人或佛陀初诞的形象。
在印度的巴尔胡特、桑奇,有许多浮雕表现了女性神站在莲花座上。有时,这位女性神的两侧还各有一头大象,象鼻子卷起水罐为她灌水洗浴,这就是当时极普遍的雕刻主题,称之为“甘迦拉克希米”(Gaja-Lakshmi)。Gaja是大象,Lakshmi是吉祥天女的名号。当巴尔胡特和桑奇在普遍雕刻这个主题的时候,佛像还没有出现,或者是佛像刚刚出现的最初一瞬。因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莲花座最初出现在雕刻图像中的时候,莲花座仅仅与印度教神系造像的一部分,与佛教无关。这就如同那伽龙王、药叉、药叉女造像大量出现在窣堵波一样,我们可以说佛教引入了这些民间俗神,却不能说这些民间俗神等同于佛教尊神。对于见惯了中国佛教造像的国人来说,往往下意识地毫不迟疑地把莲花与佛教等同起来,并不会意识到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而事实上,在古印度,尽管佛教对莲花赋予了极大的赞美,但在佛像兴起之时,莲花座却是与佛像无关的。那么,这就很自然使我们想到:中国汉晋时代的单独表现的莲花图案,是不是一定与佛教有关?
这里,我们引用德国学者齐默尔·海因里希(Heinrich Zimmer)的议论:“梵文中‘莲花’一词,kamala和padma,当带有阴性长a尾音时,意思是栖居莲荷中的女神:迦摩罗(kamala)、帕特摩(padma)。她与世界创造者和庇护者毗湿奴的佳配吉祥天女拉克希米是等同划一的。她是运气、昌盛和好命运的化身。她司管着土地的丰产和水份以及地球子宫中的宝石和贵重金属,并被表现成站在莲花之上,就像其他神祇站在他们的动物或交通工具上一样,正如公牛南迪是湿婆神性本质的动物符号、雄野鹅是婆罗门的代表一样,莲花则是吉祥天女拉克希米女神的植物符号”。
又云:涉及这一女神的最早的文学资料是所谓“室利苏克陀”(sri-sukta)赞美诗,是附加在《梨俱吠陀》古代文集增补部分的短小的晚期诗行,诗文中称女神为“莲花的持掌者,或莲花手”(padmini),“站在莲花上的人”(padmesthita),“莲花色”(padmavarra)、“莲花生”(padmasambhava)。她亦被誉称为“粪肥的拥有者”(karisini);因为她是印度本土农业中水稻生长的女守护神,这里稻谷种植在泥土和灌了水的田地里。她又是土壤丰产女神,而丰产又来自于水,并且她还赐予“财富、奶牛、马和奴隶”。为此,她又是昌盛和富足女神。她“戴配金银花环”,而且是辉煌壮丽的特别化身,赐人声望(kirtti)和成功(riddhi),并允诺兴盛和长寿、健康及子孙。她生就着莲花一样的眼睛(padmaksi),眼长怡如盛开的莲花瓣(padmadalayataksi),大腿象莲荷一般(padma-uru),有一张莲花脸(padmanana),寓于莲花中(sarasijanilaya),很是喜爱莲花(padmapriga),并手持莲花(padmahasta)。她也是“大地女神”(ksamadevi)和“所有造物之母”(prajanam bhavasi mata)。她“从大象的吹号中获得愉悦”(hastinadapramodini)。最后,她还是毗湿奴所钟爱的王后——配偶(harivallabha, visnupatni)。[6]
以上的征引,可以作为我们特别关注甘迦拉克希米(Gaja-Lakshmi)并且说明莲花座与佛教无关的注脚。我们相信,在信奉拉克希米的古印度人看来,莲花完全可以成为女神所寓示的全部美意吉兆的象征,也就是说,莲花是丰产的象征、昌盛的象征、富足的象征,等等。而且,我们能感觉到,“莲花的持掌者,或莲花手”(padmini/padmapani),是“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vara)的另一个名称,古印度观音造像,以手持长茎莲花者最为常见。观音与拉克希米,两者之间一定有密切的关系[7],尽管本文目前还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
二、甘迦拉克希米与摩耶夫人无关
女神“甘迦拉克希米”(Gaja-Lakshmi)大量出现在佛塔装饰上,作为一个丰乳肥臀的女性神,经常被认为与释迦牟尼诞生有关。这里依旧引用齐默尔·海因里希的意见,在《莲饰的象征》,他指出:“在桑奇和巴尔胡特(Bharhut/帕鲁德),有大量表现拉克希米的浮雕,她们仍保持着古代流行的神灵的象征手法。她被置于莲荷之上,由莲花环绕并手持芝花。这样的姿势并不能成为佛陀诞生的传说的根据;事实上,她们与传说中描绘的在芸果树林中的场景相矛盾。摩耶王后应该是站着的,也不是在莲花中,而是在一棵树下,就像一棵女神树、一个树精,或弗里克娑提婆多(vrkshdevata)。所以,富歇富于创造才能的阐述,其可以接受的方面仅止于理解这一特殊的情况而已。——为了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工匠不是孜孜不倦地去改变印度教法则中的任何细节以便使之与佛教传说相契合。一个同时代的人,面对它肯定不会想起释迦族的狮子诞生,而却会想起著名的吉祥天女拉克希米女神。”
吉祥天女,实际源于水的崇拜。伴随着他的大象(gaja)卷起水罐为她灌水,已足以表明她与水的联系。大象,在梵文中,或作“gaja”,或与龙王一样都写作“naga”,这也暗示了大象或克希米与水的联系。也就是说,在巴尔胡特或桑奇大塔上的拉克希米,仅仅表示渊源于印度古老传统的水女神崇拜,这种崇拜与佛教无关,更与释迦牟尼的诞生无关。在汉译佛典中,所有谈到与释迦牟尼诞生有关的传说,都谈到释母摩耶夫人在蓝毗尼花园中,举右手攀扶树枝时,释迦牟尼从她的右胁下诞生。这是借用了古代由来已久的“沙罗班吉卡”(salabhanjika)的形象。
“沙罗班吉卡意思是一位妇女毁坏娑罗树(梵语sala=娑罗树、bhanjika=毁坏树的妇女)。但是在艺术上,沙罗班吉卡表现的妇女既不是毁坏树,树也不是娑罗树。妇女只是握着一枝开花的树枝,一般是asoka或kandamba或champka或amra树枝”[8]。古印度人相信,“年轻的女性与树干一接触,树就能开花结果,女性的生育能力与丰穰相结合,故而强调乳房与臀部,裹着薄透的腰布,夸耀丰满肉体的姿势”[9]。惠廷顿(Susan Huntington)注意到巴尔胡特“沙罗班吉卡造像”的微小细节,药叉女的左手“指着她的生殖器的部分,而右手举着一根开花的树枝,树似乎是从她子宫里冒出来的”[10],这个图像很好地显示了“沙罗班吉卡女神”的寓义。
现在所见的以“沙罗班吉卡”为原型的佛诞图像,在犍陀罗佛传图像中屡有所见,而恒河流域的同类造像似乎出现较晚,所见多为五世纪前后,多为四相或八相之一[11]。因而,实在难以与甘迦拉克希米造像与佛诞联系起来,更不敢相信与拉克希米有关的莲花或莲花座与佛教有所联系。佛母之名摩耶夫人“maha-maya”,意为“幻”、“大幻”,类似于中国的“道”或“无”,颇有哲学意味,是与释迦降诞的神圣化有关。换句话说,在古印度的信徒看来,他们并不认为释迦牟尼是世俗夫妻的儿子,而是从无形无象、恍兮惚兮的宇宙本源中诞生的“宇宙之子”。这一想法,似是来自梵天信仰的启发。而在图像之中,至今所见的佛母或释迦初诞的图像,都是以“沙罗班吉卡”为原型的,与这位树女神的生殖意义相符,可以看作是借用通俗神像以表示佛教思想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把“甘迦拉克希米”解释成佛母或释迦初诞的,除了富于诗意的想象力之外,无法得到文献记载和其他图像的印证,我们不认为“甘迦拉克希米”具有佛教含义。
三、荷花与梵天造像的联系及其象征意义
当佛教造像的在古印度处于初期阶段时,佛陀的侍从主要是因陀罗和梵天。这位大神梵天与莲花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印度的古典文献中,梵天“被称为帕特摩阁(padma-ja)、帕特摩阇陀(padma-jata,意为莲花生)、帕特摩迦里诃(padma-garbha)、帕特摩瑜尼(padma-yoni,其母亲的子宫曾是——或现在仍是——荷花)。作为神性物质的创造性方面,他完全有权占有莲座,因为他是永恒之水的第一个创造物,因而是莲花女神的一个男性复本。按婆罗门哲学与神话的传统,他亦是纯粹的、精神的以及超验的自然本性的最高本体存在,这是梵的拟人化的象征,是漫无边际难以名状的宇宙本质自身”[12]。又云,“当婆罗门的观念和信条在印度占据了优势时,莲花女神只得将她的宫殿让给了梵天,并把梵天当作自身的一个阳性复本。从此,我们看到梵天篡夺了莲花宝座——它成为一个符号,座位和乘骑的工具,实际上就是女神帕特摩(padma)——拉克西米名字本身。在这个位置上,梵天方能行使象早期女神一样的功能”[13]。
在佛教信徒看来,一方面把梵天引入佛教,让他成为佛陀的侍神,以此表明与印度教对抗、提升佛教的宗教地位,另一方面,又把梵天的某些神格属性与释迦牟尼结合起来,使得释迦牟尼成为与梵天一样的具有超验属性的大神,使之从一个伟大思想家或传教者的角色转化于梵天那样的“漫无边际难以名状的宇宙本质自身”、“纯粹的存在本身,无上的事实,超越的变化、时间和各种限定的资格”的至尊大神。因此,原先与梵天相联系的莲花座,也逐渐与释迦牟尼联系起来。然而,真正站立或端坐在莲花座上的佛陀,在古印度出现得很晚。虽然难以肯定莲花座佛像出现的时间,但是至少可以明确的是贵霜时期的秣菟罗和犍陀罗尚未出现类似的佛像。
如果我们再重新阅读起源稍后的佛典,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下有这样的看法:“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住不退转,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支道林撰《阿弥陀佛像赞》甚至强调“男女各化育于莲花之中,无有胎孕之秽也”。这里所说的是芸芸众生,但又何尝不是上述佛诞观念的曲折反映呢?佛教徒不承认释迦牟尼是“胎孕之秽”的凡夫之子。诸天人民之上辈,尚能在莲花中自然化生,更何况是释迦牟尼?把莲花与净土联系起来,显然不仅仅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寄寓。梵天造像的常见形式,他是从一朵莲花上诞生的。那么,佛教关于莲花化生的观念,应当是源自于梵天信仰的。莲花座佛像,也暗示着梵天诞生那样的意义,释迦牟尼是从宇宙本源中诞生的,释迦牟尼便是宇宙本源的人格化,他是象征宇宙本源的至尊大神。
虽然上文的论述还有许多粗疏之处,大体如下的结论:在古印度的观念中,首先与莲花相联系的是女神拉克希米,这是与水相关的农业女神、丰饶女神、昌运女神、财富女神,甚至是长寿女神、子嗣女神,具有多种神格,但是,主要与财富、丰产与繁荣有关。她的形像被广为雕刻,出现的时间较早,却与佛教基本无关。莲花甚至可以替代女神本身,成为一种“象征物”,用以象征“财福、丰产与繁荣”及其他各种祈愿和多种神格。梵天,是与莲花相关的另一位大神。他是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象征宇宙本源。佛教吸纳了梵天信仰的某些神格属性,把释迦牟尼神化成了象征宇宙本源的至尊之神,在佛陀造像中也借用了与梵天相联系的莲花座。莲花座意味着释迦牟尼是从宇宙本源中诞生的象征宇宙本源的至尊大神。梵天造像出现的时期,远远晚于梵天信仰,同样,莲花座佛像出现的时期也并不很早。至少在贵霜时期的各式造像中,尚未发现明确的莲花座佛像,贵霜时期的莲花与佛教也缺乏必然的联系。
四、并蒂三莲与神舍卫城大神变
佛教造像引入莲花或莲花座的时间尚难具体查考,但佛教引入莲花座的思想动机,却是相对明确的,这与佛陀的神格化有关。如果我们更加细致地重新检查古印度的佛教造像,就会发现:首先出现的与莲花相联系的佛教造像,都是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Pratiharya-sutra=the miracles al sravasti)的造像,这实际上是无数的佛从无数的莲花上诞生的群像(似与莲花化生的观念有关),而独立的单尊莲花座佛像出现得更晚。
“舍卫城大神变”是《天譬喻经》(Divyavadana)的第十二篇,是一个独立的神话般的譬喻故事,我们已经全文译出,并结合中国的造像进行了讨论[14]。唐朝三藏法师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二十六《第六门第四子摄颂之余佛现大神通事》(收录于《大正藏》第24册,no. 1451),是同一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根据福歇的研究,出土于鹿野苑的两件造像碑,很好地表现了这个题材。
前者的千佛化现造像碑,与佛典文本特别吻合。佛陀端坐于大莲花,结说法印。佛陀化现的诸佛都居于荷花之上,荷花的梗茎如同树枝般的联系着各尊佛像,并最终与主佛座下的莲花连接起来。义净译典云:“诸龙持妙莲花,大如车轮数满千叶,以宝为茎,金刚为须,来至于此。……时彼龙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手摩地,知佛大师欲现神变须此莲花,即便持花大如车轮数满千叶,以宝为茎金刚为须,从地踊出。世尊见已即于花上安稳而坐,于上右边及以背后,各有无量妙宝莲花,形状同此,自然踊出,于彼花上一一皆有化佛安坐,各于彼佛莲花右边及以背后,皆有如是莲花踊出化佛安坐,重重展转上出乃至色究竟天。莲花相次,或时彼佛身出火光,或时降雨,或放光明,或时授记,或时问答,或复行立坐卧现四威仪”。
后者的释迦八相造像碑是一种简洁的表现形式,福歇有详细的描述:“在一朵花茎自水涡涟漪中伸出的莲花上,佛以神圣的姿势盘脚而坐,双手结说法印。在他的两侧也各升起一株长茎红莲花,莲花上各有一尊与主尊完全类似的小佛像。……按《天譬喻经》记载,在那一刻,即波斯匿王第二次请佛,而神变的第一个系列已经完成的时候,‘佛有回俗世的念头’,众神立刻争相去实行:梵天在佛右边,帝释天在佛左边,两龙王难陀和邬波难陀变化出一个完整美丽的莲花,佛坐在莲花的花冠上。然后,佛以神力‘在他坐的莲花上方,又化出一朵莲花,而且在这朵莲花上同样也有一尊盘腿而坐的佛;以同样的方式,在佛的前面、后面、侧面都出现了这种上有坐佛的莲花’,佛众各自持四种神圣的姿势之一(立行坐卧),不久就上升到最高的天宫。浅浮雕不能像经文一样,完全遵众数字和格式上的规则,因此只展示了其中三个佛,并都为坐姿。但是,至此对我们来说,尽管有此拘谨,但毫无疑问,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个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千变万化的传奇故事的一种尝试”。[15]
这两件造像,都被确定为公元五世纪。然而表现形式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很难认为这是古印度最初出现的大神变造像。海外研究大神变的论文论著,就我们阅读的范围来看,基本上都是从上文列举的两种造像为起点加以讨论的,似乎没有提到这类造像最初像例,也没有给出大神变图像最初出现的时间。本文认为,这类图像出现的时期,可以从中国莲溪寺造像中予以推求。
再度审视莲溪寺造像中的莲花座。主尊“赤脚站在由三瓣尖锐的覆莲组成的圆形莲座上。莲台两侧各向上伸出一束细长而弯曲的莲茎,上端有花苞形莲花”[16]。详细观察图像,两侧的小莲花仿佛是从中间大莲花两侧生长出来的。联系前面举出的鹿野苑八相造像碑,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属于同一种图像体系。
中印两种图像的对比,也有重要的差别:其一、武昌莲溪寺的小荷花,与中间的相比,显得形体太小,还不足以构成莲台形状。其二、小荷花上还没有出现佛像,“舍卫城大神变”以“千佛化现”为核心,在图像上至少有三尊造像,而莲溪寺造像仅有中间的主尊。介于这两点的考虑,这只能视为“大神变造像”的雏形。一方面说明古印度大神变造像的雏形始于三世纪,而正式定型很可能是四世纪,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造像源于印度,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间差”是相当有限的,也就是说,当印度兴起一种新的造像样式之时,中国也迅速涌现了类似的造像。
据“大神变造像”的文本依据和图像谱系,莲溪寺造像中间的主尊应当是佛像,而不应该是菩萨。已有的研究,颇有认同这是菩萨的,甚至有推测其造源是源于秣菟罗或犍陀罗的,由于我们辨认出“并蒂三莲”与“舍卫城大神变”之间的联系,从文本依据出发考虑,主尊不应该是菩萨,而应该是佛陀。同时,我们认为:一方面是秣菟罗或犍陀罗都缺乏类似的菩萨形象,尤其是右手举至胸前是早期佛像的特征而不是早期菩萨像的造型特征。除去部分细节上的差异,我们发现这与浙江临海建衡三年(271)画像砖佛像、时代不甚明确的沂南画像墓佛像,基本相似。另一方面,尽管时至公元262年,中国已经有了仪轨相当完备的佛像,但中国东部地区从南部交趾到北部江浙地区[17],无论是典籍文献还是造像遗物,都表现了对佛像认知的模糊性。或许是兼有这两方面的原因,他们把菩萨和佛陀的特征混淆在一起了。或许是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根本没有想到主尊到底是佛陀或是菩萨,他们并不关心两者之间的区别。
长江中下游的铜镜和魂瓶上的佛像,其时代在莲溪寺造像之后,在西晋末年之前(262—313),如前所述,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加以讨论,具有复合性的图像渊源。莲花座,是与四川地区造像的极重要的区别之一。长江中下游的佛像莲花座应当与莲溪寺造像一样,渊源于古印度,因而在造型上常有相似之处。其次是禅定印坐佛,是秣菟罗佛像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是与四川造像明显不同的重要特征,应当是从另一种传播途径接受古印度影响所致的结果,这种途径很可能南方海路交通。莲座两侧各有一个动物的头部,魂瓶佛教造像更接近于秣菟罗造像系统的双狮,铜镜造像更接近四川西王母的龙虎座,说明中江中下游造像在海路传入的印度影响的支配下,仍然多多少少地接受了四川图式的一些影响。就本文关心的莲花图像来看,在“262—313”年间,长江流域中下游接受了古印度造像的影响,正式与佛教联系地一起。
五、汉晋莲花图像的再讨论
在讨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论文论著中,常常把莲花图像视为佛教传入的证据。问题是,第一、类似莲花的图像是否能够确定地判定为莲花,第二,莲花是否一定与佛像有联系。前者已经讨论了莲花的宗教属性,认为古印度的早期莲花图像与佛教无关,那么,中国早期的类似于莲花的图案即使有够判定为莲花,也未必与佛像有关。也就是说,早期的莲花图案不足以证明早期佛教传播。
按照我们的理解,印度佛像很可能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后期[18],相当于中国东汉(25—220)前期,佛像与莲花联系起大约是三世纪中后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末期(魏,220—264;蜀,221—263;吴,222—277)。这些看法,可以从前文的论述得以证明。这是我们讨论莲花象征意义的基本依据。
中国最早的莲花图像一时不易确定,但著名的莲鹤方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当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国、佛像更是无从谈起,因而这明显与佛教无关。日本林巳奈夫研究了“汉代前后”的中国莲花图像[19],列举了92例图像,分成“所谓四叶纹就是荷花、四叶纹(莲花)与天体、天之中心的莲花、华盖星与天皇大帝、天帝与日月、莲花(天帝)与龙、天上的莲花与地上的莲花、莲花与山岳、莲花的世界”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通篇不曾涉及荷花与佛像的联系,反而列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莲花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联系。另外,也有一些中国学者从其他途径论证了莲花与中国观念的联系[20]。
在当时生活起居中,屋宇殿阁有莲花图像装饰。《鲁灵光殿赋》有“圆渊方井,反植荷蕖”等句,三世纪末的张载进行了解释(约略相当于铸造莲溪寺佛像的年代),认为“种之于圆渊方井之中,以生光辉”。也就是说,在鲁灵光殿天花板藻井上的倒垂向下的莲花,其意义是“荷花放出光辉”的。曹植《芙蓉赋》也表达了类似的意义,“其始荣也,皦若夜光寻扶桑;其扬晕也,晃若九阳出旸谷”。更多的类似文献,可参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二“芙蕖”条(林巳奈夫汉译本第84页)。
在神话传说中,有些类似莲花的图像实际上与荷花无关。《淮南子·地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也就是说建木在都广,是众帝由那儿上下的地方,一到日中便无影,发出大声而无回音,是天地之中心。若木在建木的西面,末端有十日,光华照着地下。东汉的高诱注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莲华,华犹光也,光照其下也。”意思是说,“在若木的末端上有十个太阳,其形状像莲花,花还有光,这花照着下地。所谓莲花有光辉这一观念与若木枝端十个太阳形的东西相结合很耐人寻味”(同上引)。
提到建木,这使我们想起四川东汉佛塔画像砖,佛塔两侧的图像,形似高竿,竿端似花,曾经被称为菩提树或莲花,我们认为是三宝柱在中国的讹误[21]。联想到《淮南子》中所说的“建木”,我们不能不联想到,无论画像砖图像被如何确定名称,制作者受到建木信仰的影响,都是有可以存在的。也就是说,外来图像之所以在中国安国落户,实际上是以中国固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为前提的。之所以“曾经被称为菩提树或莲花”,虽然是以“莲花图像等同于佛教”的潜在意识为默认前提的,但却没有考虑到与佛塔伴生的具体情境以及“东汉后期”这一具体的时代因素,我们也正是基于这两点将其判定为三宝柱的。这样说来,画像砖上佛塔两侧的图像,虽然形似莲花,实际上并不是莲花,而是以建木为基础对三宝柱加以改造的结果。
由《淮南子》又想到摇钱树佛像上的花朵模样的图像。有一种观点认为,“莲花与佛像的组合,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汉中期的四川安县和城固摇钱树枝叶佛像上面,佛像头顶有中央的侧立莲花和两侧的俯视盛开莲花,佛两侧则有侧立莲花,这些莲花均由藤茎之属连接,形成佛像的背屏”[22]。我们难以认同这种看法。摇钱树渊源于古印度的劫树,是圣树崇拜在中国的再现[23],现在看来,未尝不与建木有关,或者说,中国之所以制造青铜摇钱树,大概是与建木信仰混同在一起的。具体到安县摇钱树中的花朵形状的图像,或许是建木顶端“状如莲华”的艺术化的反映。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至少在目前没有发现佛顶头光之外再有莲花表现的像例。因此,把这些花朵判定为莲花,既缺乏相应文献依据的支持,又难以得到印度同类造像的支持。
另一件“莲花祥瑞花纹砖”,四川彭山汉墓出土,影印于《佛教南传之路》第24页。据前引林巳奈夫的论述,这是“四叶纹”(柿蒂纹)演化而来的图像,无论是四瓣或八瓣,“都是当时表现莲花的方式”,通过具体的图像分析得出了“所谓四叶纹就是莲花”的结论(林巳奈夫汉译本第79页)。介于这类图像在中国传承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因而,我们认为这类图像是战国以来顺序演变的结果,是四叶纹的繁化,难以认为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又因为同墓所出文物都没有明确的佛教属性,加上砖画的花朵图案是与中国祥瑞图像组合而成的,所以,我们也并不认为这方画像砖上的图案与佛教有关。
似乎不必讨论太多的像例,在古印度佛教与荷花发生联系及其在中印两国发展的大框架下,我们认为中国东汉三国的许多独立出现的莲花图案,与佛教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关于莲花的定名也多有望文生义之嫌。但是,长江中下游的莲花座却是明显与佛密有关的,这既得到了印度相关造像的支持,也为印度佛教造像史的缺失环节进行了有效的补充。莲花与莲花座,并非一回事,这也是本文努力把莲花图像与莲花座区分开来加以讨论的原因所在。
六、结论
我们希望通过莲溪寺造像的莲花座这一造像细节,考索莲花座的古印度渊源,认为这是“舍卫城大神变造像”输入中国的结果。同时,认为印度早期的各种造像中,莲花与佛教基本无关,相应地,中国早期图像中的莲花,也与佛教无关。通过造像与文献的双重考据,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古印度造像最先出现莲花座的,是女神拉克希米(Lakshmi)。这是早期流行的女性神像之一,大量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的巴尔胡特或公元前后的桑奇大塔中。但是,女神和莲花座自身,都没有佛教属性。后来出现的梵天造像也同样拥有莲花座,其宗教属性与拉克希米相近。
第二,观世音的特征是手持莲花,他与拉克希米有关。虽然观世音造像出现时间或早期流行情况并不清楚,但是,这是荷花被引入佛教的一个显著标志,观音是与莲花有关最受欢迎的菩萨。推崇观音信仰的《妙法莲花经》使用“妙法莲花”作为书名,应当并非仅仅作为形容词或赞美语出现的。
第三,虽然我们不能详细了解所有的像例,但是,海外学者关于“公元四世纪前的佛像没有莲花座”的论点[24],仍然给我们确定佛像莲花座出现的大致期限产生了很大的启发。至少,我们在秣菟罗流派和犍陀罗流派的早期佛像中没有看到莲花座。莲溪寺造像“永安五年”的准确纪年,能够证明古印度“至少在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时佛教造像已经有莲花座”了,希望这也是我们对印度造像史研究的一点微薄贡献。
第四,莲溪寺造像是“并蒂三莲”,两侧的小荷花之上没有佛像出现。这种形式是“舍卫城大神变造像”的雏形,并由此可以依据《天譬喻经》判断出造像主尊是佛陀而不是菩萨。
第五,倘若回顾“舍卫城大神变造像”的图像谱系,已有的研究都是从公元五世纪的像例开始的。从中国莲溪寺造像来看,这一图像谱系至少从公元三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出现雏形了,希望这为我们一直孜孜讨论的“舍卫城大神变造像”图像谱系增加一个起始判断的编年标尺。
第六,综合考虑以上各项,就会清晰地显示出莲花座如何被引入佛教并传入中国的大致框架:处于雏形阶段的大神变造像,经南海传入中国,在中国得以的一种模糊的似是而非的表现。
第七,中国东汉三国的许多莲花图案,是战国四叶纹的延续和发展,与佛教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无法得到古印度相关造像的支持,不能成为佛教研究的证据。莲花与莲花座,不宜混为一谈。
以上各项,有些还没有十分成熟的意见,而是直接引用海外学者的研究作为我们论点的佐证。我们通过对中印早期造像的整体性的综合认识,确信已经建立了一个大体合理的框架体系,我们也自信,现在所缺少的只是没有引征更多海外学者的看法(尽管大可不必旁征博引),也缺乏直接征引印度古老文献的能力(尽管这一遗憾可以使用印度早期像例得以有效的弥补)。
注释:
[1]阮荣春: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东南文化》1990年1期。《佛陀世界》,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佛教南传之路》,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2]罗二虎:《重慶で新発見の紀年錢樹の仏像にっぃて(重庆新发现的纪年摇钱树佛像)》,龍谷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43集,2004年。
[3]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汉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4]宿白:《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按,宿白此书是他1982年的讲稿。又,“奥高遗址”云云,未详。
[5]阮荣春:《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
[6][德]齐默尔·海因里希:《莲饰的象征》,李建雄、张亚莎译,《西藏艺术研究》,1994年3期。
[7][德]齐默尔·海因里希:《莲饰的象征》,“观世音菩萨亦以钵特摩波尼(padmapani,莲花手)‘手持莲花’而闻名”。“拉克希米的莲花、难近母(Durga)的狮子以及湿婆的三叉戟作为观世音菩萨的主要象征,甚至还要分享难近母与拉克希米的女性美,观自在菩萨是一个印度教至高无上的神性力量的综合体现。所以他能满足众多世俗的信仰与情感需要,这些民众虽已转向了佛教团体,却仍墨守着流行的印度宗教古老遗产的常见形象”。
[8]Kushana Sculptures from Sanghol. Edited by S. P. Gupta, New Delhi, 2003。
[9]肥塚隆:《贵霜时代的秣菟罗雕刻》,《ィンド·マトゥラ一彫刻展(印度秣菟罗雕刻展图录)》,日本东京:东京博物馆,2002年。
[10]Susan Huntington, The Art of Ancient India: Buddhist, Hindu, Jain(古印度艺术:佛教、印度教、耆那教)。Weatherhill, 2006. P. 69.
[11]我们所见的在摩耶夫人腋下释迦初诞的造像(其他“二龙灌水”之类出现得较早,中国笮融浴佛也没有提及摩耶夫人),最初出现在五世纪,如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四相碑(s 3/a25098)、新德里博物馆藏佛传造像碑等。均出土于鹿野苑,也都是四相或八相的一部分。还有更早的造像,尚待调查。据Kushana Sculptures from Sanghol(Edited by S. P. Gupta, New Delhi, 2003),沙罗班吉卡“这个习语出现在比哈尔北部和尼泊尔南部。这里到处是娑罗树林。在蓝毗尼园(现尼泊尔),乔达摩佛神奇地从摩耶夫人胁下诞生,这个情节在犍陀罗、秣菟罗、萨尔那特艺术中反复表现。几乎所有摩耶夫人都是三屈式(tribhanga)姿势表现,站在娑罗树旁,举着一根开花的树枝。这个想象的故事,大致上也是受萨罗班吉卡影响的形式,至少影响了一部分。”
[12][13][德]齐默尔·海因里希:《莲饰的象征》。
[14]张同标:《中印佛教造像探源》,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
[15]福歇:《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王平先、魏文捷译,银川: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16]何志国:《论武汉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出土的鎏金铜牌菩萨像》,《艺术与设计》,2010年第1期。
[17]成书于交趾的《牟子理惑论》(收入《弘明集》卷一)对佛教的认识,尽管极富热情,但对佛陀形象的认识是模糊的。吴主孙皓对着尊像小便以及宫娥“佛为大神”(《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的认识,也同样是模糊的。
[18]张同标:《中印佛教造像探源》。
[19]林巳奈夫:《中国古代莲花的象征(一)》,蔡凤书译,《文物世界》,1999年第3期。按,未见译文续篇。日语全文:《中国古代におけゐ莲の花の象征》,《东方学报》,第59卷,1987年第1期。
[20]卢丁:《莲花纹瓦当考》:“莲花纹样是中国本土汉代就有的美术图案,那时的寓意是本土宗教的司水神的圣物,有避邪防灾咒术的意义”。按,印度早期造像的莲花也与司水神有关。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9—342页。
[21]张同标:《中国早期楼阁式佛塔及其渊源》,《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
[22]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222页。
[23]张同标:《古印度劫树与中国四川摇钱树的联系》,《中外美术研究》,2010年第5期。
[24]Asian Art at the Norton Simon Museum. Volume 1, Art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Pratapaditya Pal, Yale University, 2003。前言第20页:在印度文学和艺术上最流行的植物是粉红色的莲花,在用于对身体和精神之美的隐喻的偏爱上具有同等的卓越性。在公元前3世纪的女人陶像雕刻上,显著地表现了花萼作为装饰,而在公元2世纪的浮雕,靠近佛陀的一组奉献者手中拿着莲花。神和天神们通常被称为在散播在莲花的道路上行走,而且特殊的吉祥行为,例如释迦牟尼的出家,通过一位神祇展示的一朵花来表示。无疑直到公元4世纪,莲花开始成为支撑神祇的典型,无论坐的或站的。然而,较早期,只有女神,主要是拉克希米(Lakshmi),繁荣的分配者,具有一个莲花座支撑。在早期文学中,她的住所往往描述为莲花房(kamalavasini; kamalalaya)。
责任编辑:小萌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