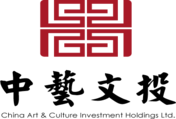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的现代化
2014-07-23 15:36:16 作者:吴宏一 来源:中华古籍网 已浏览次
一
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往往自诩历史悠久,文化昌明。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冠冕堂皇,颇能振奋民族的自尊心。不过,历史越悠久,文化越发达,对于想认识传统文化的人来说,事实上却反而是越难承担的历史包袱。大家试想想,中国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语言文字已经多所差异,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更是迭经变革,对于现代人来说,想要了解这千百年以前的历史文化,真是谈何容易!特别是被奉为经典宝库的古典文学和古代文献,现代人想要去接触它,了解它,更是不知从何下手才好。
这里头的困难,古人早就说过了。像郑樵《通志·艺文略一》就说: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①
戴震《尔雅文字考序》中也说: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②
就因为时代不同了,古人一听就懂的事物,后代的大学问家转相考证都还不明白,所以后人读古书,不仅“事物难明”,而且也往往“理意难明”。用现代的话说,这困难至少有两点:
(一)这些古代文学文献的作品本身,以文言为主,而且对于一般人而言,多数古奥难懂,阅读上有困难。尤其是古书中不少奇文异字、生僻典故,非专家学者,字音不会念,词义不了解。王国维是近代着名的大学问家。他曾经说他自己读《诗经》有十分之一二不懂,读《尚书》有十分之五不懂,并且分析其故,说是或因字句有“讹缺”,或因“古语今语不同”,或因古人“颇用成语”,而“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③连大学问家王国维都觉得古书阅读时有困难,也就难怪一般人会对古书望而却步了。
(二)因为古今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有所变迁,因此古人作品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情感,现代人不容易体会。举例来说,像《国语·晋语》中,写骊姬乱晋时,太子申生虽然知道骊姬的用心,却因为怕他父亲晋献公伤心,既不敢揭发,又不敢逃亡,最后白白送死。④这样的“愚孝”,不少现代人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像唐代传奇《李娃传》中,写郑生为李娃抛却功名,沦落凶肆之中唱挽歌时,被父亲发现了,认为有辱家门,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丢在路旁。⑤这样的“亲情”,不少现代人一定也会觉得不可思议! 事实上,这都跟古人的孝道观念有关。不明白古人的孝道观念,就不能明白这些故事的道理。⑥也就因为古人的思想方法、道德观念,未必与今人相合,⑦所以现代人想要认识古代的历史文化,必须先了解古人的思想观念。即使是一个词语,它都可能与古人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譬如说,“风流”这个词语,古代有时候作风俗教化解,有时候作风化流行解,有时候指个人的仪表文采,有时候则指行为不拘礼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和用法,现在则多用之于指男女之间的轻薄浮夸。⑧要是不明白它随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义,只是以今律古,执一以求,想要读通古书,了解古人,几乎不可能。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历史越久远的,越需要有现代化的诠释,才可以帮助现代日趋西化的一般读者,克服阅读上的困难,进而认识这些文化遗产的宫室之美,百官之富。郑振铎《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而努力》一文说得好:有的古典文学,离得年代太远了,其“语言”本身就发生了好些障碍,非加上明白晓畅的注释,是不容易叫现代的读者们读得懂的 (像《诗经》、《楚辞》),或有许多当时的“方言”、“行语”、“前代故实”之类,也是必须加以疏释才会明白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⑨真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有人说:“整理古籍,经史子集。文代所萃,学业所积。”要整理经史子集这些浩瀚无尽的古籍,自非学有专精的专家学者莫能办。韩愈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现代人想要阅读古籍,认识宝贵的文化遗产,实不能不仰赖专家学者的协助。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认识传统的好处,而文化的道统,也才能薪火相传下去。对于古代文学文献,加以现代化的整理疏释,最常见的有两种:一是译注,重在翻译或注明音义;二是诠评,重在阐发道理或评介事物。这两种方法,古人皆已有之,不过,这里强调的是现代化的诠译。换句话说,要现代人都看得懂。郭绍虞《对整理古籍的一些建议》一文有云:考虑到当前一些青年学习古籍有困难,建议把一些重要的作品翻译成语体,以利于广泛传播。有些作品,如诗词,翻译有困难,则可以加些通俗性的注释。
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中也说,要研究国故,必须具备“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而且要懂得如何“整理”。在形式方面,要把古书加上新式标点符号,分开段落章节;在内容方面,要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说法。最重要的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
以上所说,多就据原典加以译注而言。另外的一种方法,所谓诠评,则是把原典及相关资料融会贯通之后,作概括的说明或评述。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曾引章学诚《与汪辉祖书》的话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
诠评正是要做食叶之后抽丝的工作。以《论语》首章为例,解释“学而时习之”的字义词义,解释“有朋自远方来”的“有朋”宜作何解等等,或将原文译为白话,这是属于译注的工作。至于把整部《论语》及孔子相关资料都融会贯通之后,用自己的话来评介孔子所说的为学之道,那就是诠评。本文题目所说的诠释,包括译注和诠评二者,其意义之不同,即在乎此。关于这个,下文还有补充说明。
我以为要帮助现代的一般读者,认识古代的文学文献,这是最基本的两个工作,也是到目前为止,关心中国人文发展的专家学者,所应努力的两个方向。
二
诠释的工作似易而实难。
先说注释方面。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注释工作,自古有之。从汉儒的经典训诂,到清人的校勘考据,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色,也各有其成就。不过,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的注释者,都必须把握住一个共通的原则,那就是要认清读者的对象,了解读者的语文程度。生僻的语词,罕见的故实,读者可能不了解的地方,才需要加注,否则就是浪费笔墨了。
譬如说,毛《传》、郑《笺》是汉儒解释《诗经》的着作,他们所注释的字句,一定是当时一般学者不懂得的地方。后代的学者,对《诗经》更陌生了,对于毛《传》、郑《笺》的注释文字本身,也有很多地方看不懂了,所以六朝唐宋以下,有不少注疏、集注、汇解之类的着作相继问世,来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现代一般人,要读《诗经》,不要说对原着大多看不懂,连历代的传笺注疏,也多看不懂了,必须依靠专家学者用浅近的文言或通用的白话来注解来说明,才能阅读。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所以,古代文学文献的诠释工作,特别要切合时代的需要。就今日一般读者的语文程度而言,注释最宜采用浅白易懂的语体文。否则,不容易普及。
采用浅白易懂的语体,最忌冗长芜蔓,因此,注释文字要力求简要、明白、正确。郑振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感叹说:过去有了不少注释的书,像《诗经》,就有了不下千种的历代的注家,像《楚辞》,也有了不下百家的各种的注本。有的还对我们很有用,但有的却是糊涂得很的胡说八道,令人越看越不明白,最需要注解的地方是不注的,或注得糊里糊涂的,但不需要解释的地方,却又注得很多。
像所谓“红学”那样的牵强附会,转弯抹角做索隐工作,也实在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之举。
郑氏所言,针针见血,指出了历来注家的种种缺失,值得注意。
注解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原文,除了所用文字要力求简明正确之外,千万不可藉此卖弄学问。譬如说,《木兰诗》首句“唧唧复唧唧”的“唧唧”一词,历来注释至少有三种,叹息声、机杼声、虫声,三种解释都有人主张,假使由你来做注释,你是采取其中的一种呢?或者将三种和盘托出,都告诉读者,让读者自己采择呢?我以为对中小学生语文程度较差的读者,只告诉他其中一种,说明采用的原因,可能比告诉他三种历史、让他无所适从的好;对于文程度较高的读者,当然能提供的资料,多多益善。同样的道理,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首章首句“小山重叠金明灭”一句,历来有眉山、屏山、枕山、发饰等四种解释,当你面对不同的读者对象时,你也应该有不同注释方式的考虑,不可一味以多取胜。
以前,我主编过台湾教育部编译馆出版的中小学国语文教科书,深刻地体会到上述考虑的重要性。像“不速之客”,在中学课本里头,解释为“不请自来的客人”就可以了,顶多加个注“速,催请”即可,要不然,再多引用一些先秦古籍如《仪礼》中常见的“速宾”等词,以为佐证,就应该不成问题。但这个成语,如果出现在小学课本里,光解释为“不请自来的客人”,恐怕是不行的。因为“不请自来”四字,对小学生而言,仍嫌深奥了些。
因此,注释应该扣紧原文的上下文意,而不须炫弄才学。古人所以嘲笑“博士卖驴”的原因道理在此。对初学者而言,与其对《尚书》“曰若稽古”四字,用了几万字来解释,不如不求“甚”解的好。
至于那些只会查查工具书,转引抄录一些现成资料,可能自己都不明其意,而美其名为注解的人,更等而下之,是自欺欺人,这里就不赘论了。
要做好注释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必须要有基本的版本知识,要能掌握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更应该处处留心,检讨改进。例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原名叫端木赐,我从小读书,就对此有疑问。子贡的“贡”,是下对上而言;端木赐的“赐”,则是上对下而言,意义并不相同。为什么端木赐要字称子贡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读《礼记·乐记》,读到子贡向师乙问乐,文中的子贡,却作“子赣”,才色然而喜。赣,即赐之意。现在河北定县古本《论语》出土,可以确知“子贡”,古本正是原作“子赣”,这才解决了我多年来的疑惑。以前我译注《论语》,于此阙而不注,以后若再有机会介绍子贡,自当据此补充说明。
下面说明我对古书今译的看法。
上文引用过郭绍虞的《对整理古籍的一些建议》。他以为把古籍翻译成语体,有利于广泛传播。这意见当然是对的。相传玄奘翻译佛经时,就表明“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清末民初严复等人,在译介西方科学新知时,也标榜“信”、“达”、“雅”。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通俗又何妨?更何况“通俗”与“俗”的意义是不相同的。俗,或许有贬义,通俗则是说让俗人明白而已。让俗人明白的事情,可以不俗啊 !因此,有人排斥把古籍翻译成白话,那是高自位置,不切实际的说法。
陈蒲清在《文言今译教程》里说得好:有人轻视古书今译,认为有注解就行了。其实注解并不能代替今译。注解是一词一句,零零星星,必须有一定的基础,才能借助注解读懂原文。
古书今译则是将整篇整段原文加以翻译,比较容易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概念。陈蒲清还进一步指出,翻译有直译和意译之分。直译扣紧原文的语词和句子,比较容易保留原文的句型和韵味;意译则可以改变语句的原来结构,甚至随着译者的体认,可以统摄语段大意而自铸新词新句。二者各有各的好处。我个人的看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最好用直译。因为在一字一句对译的时候,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譬如说,上文提到过的《李娃传》,它开头的句子是“国夫人李娃者”,我就因为采用直译的关系,才会一字一词的仔细琢磨推敲,考虑到前四字到底应该断为“国夫人”或“ NFDA4国·夫人”。假设是意译的话,求其译文流畅,对原文只取其大意,我想我只会把它当做李娃的封号,不会细加考虑求证的。
另外,还有人主张看古书,抛开一切注释翻译,直看原文即可。这当然自有其道理,用俗话说,免得看别人译注多了,被人牵着鼻子走。但这是对有旧学根柢的专家说的,不适用于一般的读者。一般的读者,若是根柢不深,看古书而只看白文,不参考别人的注译或翻译,我想看白文的结果,也只是“白看”而已。
三
其次,说诠评部分。
诠评的基础,固然在译注上,但二者又有不同。注释的对象是字句,所以要扣紧原文,注明音义,为读者解答疑难;翻译的对象是全书或完整的章节片段,但它只是将原着者的意思,用另一种浅白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已,与注释可以互补,却不能互相取代。它们都多少受到原文的限制,诠评则不然。诠评可以说是已经经过注释语译的阶段,对原文或原书提出一种研究、评论性质的看法。它讨论的对象,可以是一本书,一个人物,也可以是某一个专题。它要求的不是简要,而是详尽。它在讨论问题时,要广泛征引材料,多作比较,多加分析,以求深入。有关古典文学古代文献的许多专题研究论着,以及古代人物评传之类的着作,都可归入此一范围。
在从事诠评的工作时,学者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态度不够客观。举例来说,有人在评介庄子时,就说庄子最伟大;在评介韩非子时,却又说韩非子最伟大。同样的情形,有人在研究李白时,就强调说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等到后来研究李商隐时,却又强调说李商隐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样的态度,就不够客观。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崇古贵远太过,往往把所要评介的古人,视为出神入化,无所不能。于是,在他们的诠说之下,司马迁不只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军事家,上穷天文,下穷地理,几乎无所不能。同样的,苏轼在他们的诠说之下,不只是诗人、词人、文学家,而且也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有什么什么的专家。这样的评介诠说,会误导读者,也会混淆事实。
在我想来,杰出的人物当然有兼人之能,可以具备多方面的长处,但总有一个主体,一个最受大家肯定的部分。我们要介绍给一般读者的,就是这个主体,这个最受大家肯定的部分。而不是把所有的杰出人物,都说成通人,说成无所不能。因此,对文学家,应该重在说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对思想家,应该重在阐发他卓越的思想。用这样的态度,来诠说古代文学文献资料,才能给予各种事物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态度要客观之外,资料的运用也不可等闲视之。资料搜集,当然越齐全越理想。譬如说,有人谈“西昆体”,只根据有限的资料,以为它专指北宋初年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的作品而言。事实上,它的取名虽与杨亿所编的《西昆酬唱集》有关,但它往往兼指李商隐等人所作。需要多搜集相关资料,才能下判断的。资料搜集不齐全,下判断时,考虑可能就不周全。但更值得戒惕的是,不可凭空立说或妄下断语。例如多年前,台湾有一位知名学者把李白“但愿一识韩荆州”的“韩荆州”当做韩愈,把《红楼梦》当做金圣叹所批才子书之一,一时就传为笑柄。
还有,通常在评介诠说时,难免会引用原文。这些原文,往往是今人视为深奥难懂的文言。在征引时,如果能够注明出处,便于读者寻检;如果能够加以语译,或在引用之后,用简单的几句白话综述要点,便于读者理解,都是现代一般读者求之不得的。
不同于注译和翻译,诠说评介某一人物、某一本书或某一专题时,不但文字要畅达,说理要明确,更重要的是,要富有研究、批判的精神。郑振铎以为:研究、批判一部作品,就必须研究其作者,要研究作者,就必须研究、了解作者的时代。
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的研究基础,才能像庖丁解牛似的,抉发其真相,阐明其真实的意义。这也就是前人所谓的“论其世”、“知其人”,而且也和上文引过的,胡适所谓“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互相呼应。这些虽是老生常谈,但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特别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论世知人”的时候,最忌流于公式化。譬如说,写北朝民歌的论文,用不着把北朝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原原本本详说一番,除非所说与所研究的民歌有直接的关系;同样的,论析《红楼梦》的人物刻画技巧,也用不着把曹雪芹的生平和时代详说一番,除非所论与所分析的艺术技巧有关。我看过一些论着,都是先设好框框,先立好章节,然后才去找材料填补的。这样的研究,这样的诠说,不要也罢。
最后,不能避免要谈到是否应用西方现代理论方法的问题。关于这个,我以前写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一文,已经多所指陈,并且引用了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里的一段话来说明: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的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陈氏之言,虽然稍为激切,但却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对于外来的理论方法,我一直有个信念:输入不可耻,输出也不必骄傲。我们只问适不适用。如果适用,将使所欲阐述的道理,更加明白,更有说服力;如果不适用,那就是削足适履,弃之可也。
四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现代诠释,可谈的当然不止上述的这些,但是,上面所论述的,无疑是最基本的一些问题。为现代人来诠释古代文学文献时,无论是注释、翻译,无论是评介、诠说,都应该注意到把握上面所说的时代性、通俗性、准确性,都应该注意到诠释的工作,是为什么而作,为哪些人而作,怎么作才理想。能够如此,相信对现代的一般读者,一定多少有所裨益。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