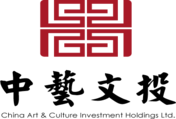鸿宝浮沉——大盂鼎大克鼎流传记
2015-01-08 09:28:02 作者:董少东 来源:北京日报 已浏览次
鼎,《辞海》上的解释是,青铜器之王。
中国青铜重器中,大盂鼎和大克鼎,是两件被称为“重器鸿宝”的西周铜鼎,与毛公鼎一道,并誉为“海内三宝”。如今,这三只宝鼎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作为镇馆之宝,引人们驻足、流连、惊叹。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盂鼎和大克鼎在清晚期出土后几经流转,曾经归一人所有,聚首北京;出土自陕西的二鼎,又曾经被深深掩埋在苏州一条幽静小巷深处,躲过了侵华日军的劫掠。
1951年,大盂鼎、大克鼎鸿宝重现。鼎身上清晰的铭文和斑驳的铜锈,默默诉说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而它们出土后的坎坷命运,隐隐折射着中国近现代的百年沧桑。

大盂鼎
掘地藏宝
1937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子夜时分。
中秋节刚过,月亮亮似银盘,为已经陷入沉寂的古城苏州洒下如霜的月光。
在这座古城中心,一条名叫南石子街的小巷深处,五个身影借着月色,在一座深宅大院中窸窸窣窣地忙碌着。
宅院的女主人叫潘达于,就是她在指挥着一项绝不能被外人所知的工程。参与者是她的姐夫潘博山及姐夫的弟弟,还有两个家中的木匠长工。
一间屋子地面正中的方砖被撬开,露出两米见方的一块土地。四个男人轮番上阵,用铁锹向下挖掘。
寂静的夜里,若有金石碰撞之声必为左邻右舍所闻。四个人的动作都是轻手轻脚,悄无声息。挖掘出的土石,或铺在院中大松树下,掩做培土,或四散在院落东侧的私家花园中,不留任何痕迹。
足足挖了两夜,几个人才在屋中掘出了一个一人来深的土坑。两个木匠把事先钉好的一个木箱置入土坑。随后,几人合力从旁边的屋子中抬出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鼎,慢慢放入木箱中。另一只体积、重量相差无几的大鼎也被抬出,呈对角线放入了木箱。
这两只青铜大鼎,即为大盂鼎和大克鼎。到潘达于这里,已在潘家传了三代。清朝晚期从陕西出土的这两只宝鼎,再一次被掩藏于地下。潘达于寄望着这个“大土坑”,能够让两只家传宝鼎躲过日益迫近的战火。
1937年的那个中秋节,没有让中国感受到任何节日的喜庆。中日淞沪会战激战正酣,焦灼着每个中国人的心。距离上海不足一百公里的苏州,从战事一开便被列入战区。战争的阴云早已把这座秀美的江南古城变成一座危城。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打,8月14日苏州即遭到日军飞机轰炸。
至9月时,淞沪会战进入胶着状态。战局风云莫测,上海危在旦夕,而苏州已成累卵之势。姑苏古城,几乎每天都在日本航空炸弹的爆炸中震颤、呻吟。
在兵荒马乱带来的惶恐中,潘达于本已随着亲友逃到太湖边上的光福山区避难。但终究放心不下藏在家中的宝鼎,中秋节前,又冒着轰炸偷偷跑回了家。
家中所藏文物古董、古书字画数量甚巨,特别是大盂、大克二鼎,至为珍贵,又体型巨大,仓皇逃难,不可能将其携在身边看护。万般无奈之下,潘达于想出了将它们埋藏在地下的主意。
然而这个办法是不是能够确保两鼎安度战乱无虞,谁也不敢保证。
2007年8月,潘达于老人以102岁高龄与世长辞。老人的孙子潘裕达今年都已经年过花甲,他与潘达于共同生活时间最长。埋鼎之日距今已七十多年,潘裕达这样对记者说:“好婆(奶奶,苏州方言)回忆往事,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埋鼎的那两个晚上,每次说起来都仿佛历历在目,每次提起来又后怕。那个战乱的年代,走漏一点风声,大盂鼎、大克鼎肯定就留不住了。”
在潘达于的记忆中,那两个晚上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只是洒下的月光泛着惨白,在寂静的夜里更让人心生凉意。
明亮的月光,倒是为埋鼎的五个人提供了天然的照明。因为日军轰炸,电灯早已断电。为了避免在夜色中引人注意,五个人干脆连蜡烛也没有点,两晚的忙碌,全仗月光。
大盂鼎和大克鼎放到木箱中后,他们又在木箱的空隙处,安放了一些小件青铜器和金银物件,左右再以旧衣物塞实。最后,木匠把木箱盖封好,平整泥土,上面再按原样铺好方砖。
潘达于又撮来一些浮土,在方砖上撒了一层,用笤帚轻扫几遍,用浮土填实方砖间的缝隙。这片地面就看不出任何撬动过的痕迹了。
这还不算,潘达于选择的埋鼎地点,处于庭院第二进院落正房的堂屋正中,原本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埋好鼎后,潘达于把这张八仙桌摆放回原处,又添了一道遮人耳目的掩护。
知道埋藏宝鼎秘密的,只有经手埋鼎的五个人。潘达于找到的四个帮手,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潘博山及其弟弟,是潘氏宗亲中至亲至近之人,潘博山还是潘达于的亲姐夫——潘达于娘家姓丁,其姐姐丁燮柔也是嫁入潘家。这两人自然可以放心。
那两个木匠,是潘氏大家族的长工,为人忠厚。为了保密,潘达于还对两位木匠师傅承诺——潘家会奉养你们一世。而这两位木匠,真的对埋鼎一事
守口如瓶,始终未向外界吐露半字。
所有的工作做完,意味着两只宝鼎从此从世间消失。曾经让潘家荣耀无比的“海内三宝有其二”之说,似乎就只剩一个传说。
“海内三宝,潘有其二”
大克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该馆坐落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丛林中,上海博物馆古朴庄重的中国古代青铜大鼎造型颇为惹眼。在这座号称“收藏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半壁江山”的博物馆中,大克鼎亦是当仁不让的镇馆之宝。
大盂鼎,原本也是上海博物馆藏品。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大盂鼎入藏国博至今,同样也是馆藏重器。
而这两只国宝级旷世文物,在百余年前居然能够同归潘氏一门所有,单这一点,已足令人惊叹。
苏州自古就是人才辈出之地,在这座“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的古城里,潘氏家族仍算得上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有所谓“苏州一座城,潘氏占一半”之说。
潘氏有“富潘”和“贵潘”之分,富潘以经商致富,贵潘因科举及仕途显赫而闻名。在清代中晚期的百余年间,潘家共有35人金榜题名,其中有1名状元、2名探花,在官场中有4人是正从二品以上的显贵政客,各地的中下级官吏更是数不胜数。“贵潘”一脉的为官之人,做遍了清廷六部九卿百官(文官)。当时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李鸿章曾为潘家题匾:“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
清咸丰二年,潘家祖字辈中的潘祖荫,高中探花,后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
潘祖荫不但在官场上位极人臣,同时又是当世著名的金石、书画、古籍版本收藏家,只要听说有善本图书、青铜文物,就“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潘祖荫在北京为官期间,居于米市胡同,府中有专藏珍本书籍的“滂喜斋”和专藏青铜器的“攀古楼”,所藏图书、金石之富冠绝于世。据说,因为对文物有着火眼金睛一般的鉴别力,他在收藏界还有个“潘神眼”的外号。
而潘祖荫的“神眼”不但能鉴文物,识人更是独具慧眼。“晚清三杰”中最放异彩的左宗棠,由一介书生而出将入相,彪炳史册,就与潘祖荫的鼎力举荐大有关系。潘祖荫也因对左宗棠的举荐,而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藏品。
话还要从左宗棠尚未发迹时遭遇的一次危难说起。清咸丰十年,在湖南巡抚幕僚府中襄理军务的左宗棠,因为恃才傲物,触犯官场众怒,遭人上奏诬告弹劾。咸丰皇帝命湖广总督密查左宗棠,如确有不法之事,可就地正法。
就在此时,与左宗棠并没有直接交往、却深知左宗棠才能的潘祖荫站了出来,三次上疏保荐。后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对左宗棠的赞誉之词:“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即出自潘祖荫之笔。
后来,左宗棠平步青云,终成一代名臣。而对在关键时刻向自己伸出援手、仗义相救的潘祖荫,左宗棠自是感恩戴德。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西安得到大盂鼎,将其赠给了潘祖荫。
大盂鼎是西周周康王时期的重要青铜礼器,也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最大的一件铭文铜鼎。大盂鼎通高1米有余,口径近80厘米,重逾150公斤。鼎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整个大鼎工艺精湛,造型雄伟凝重,自成威仪之象。
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在当地的士绅、官员手中几经流转,后被左宗棠幕僚以700两白银购得,并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知道潘祖荫是当世收藏大家,爱青铜器如命,遂以大盂鼎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
潘祖荫得到大盂鼎,自然喜不自胜。他请晚清金石大家王石经操刀,给大盂鼎专门篆刻了一颗“伯寅(潘祖荫字)宝藏第一”的巨印。
据后人考证,潘祖荫得到大盂鼎是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16年后,他又得到了另一件旷世奇宝——大克鼎。
大克鼎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径75.6厘米,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字体工整,笔势圆润,是青铜器铭文典范之作。
大克鼎于1890年(一说1889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一同出土的是一个青铜器物群,据传总数超过千件,当日即被瓜分,四方流散。其中器型最大、最为华美的大克鼎流入天津,被金石收藏家柯劭忞购得。
柯劭忞是潘祖荫故交。得知柯劭忞有大克鼎入藏,潘祖荫欣羡不已,几番登门拜求,终于重金购得。
至此,大盂鼎、大克鼎两大青铜至尊礼器同归潘祖荫所有,“攀古楼”所藏当世无出其右者。潘氏一门,至潘祖荫一辈,官爵位极人臣,家藏富甲天下,可以说达到了家族荣耀的顶峰。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潘氏家族的辉煌顶峰也是衰落的开始。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年底,潘祖荫撒手人寰。潘氏一族再无入朝为官之人,原本庞大的家族也变得人丁零落。
藏于北京“攀古楼”中的大盂鼎、大克鼎,失去了权贵主人的庇护,在乱世之中,无异于被豺狼环伺的羔羊。
“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潘祖荫病逝于1890年年末,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由于二人终生未育子嗣,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比他小了整整40岁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
当潘祖年得悉嫂子去世,从千里之外的苏州赶到北京奔丧,时间已经过了一月有余。就在这段时间,“滂喜斋”、“攀古楼”中已有大量藏品被盗。
潘裕达说:“好婆曾听我的曾祖祖年公说起过,当时明确丢失的是几套完整宋版书的第一册。这应该是家贼所为,拿了那些书出去估价了。如果不是曾祖赶到,恐怕还要丢失更多。其余的零散藏品究竟丢了多少,更查不到了。”
潘祖年顾不上追查被窃的藏品,匆匆处理好善后,将潘祖荫的藏品和灵柩一同装船,顺着京杭大运河运回苏州。其中就有著名的国宝大克鼎和大盂鼎。另有铜钟和铜鼓两大件,因又大又重无法搬运,只得就地送了人。不过,潘家后代分析,以潘祖年对兄长藏品的珍视,绝不会将这两件宝器轻易流转他人。送出铜钟和铜鼓,或许就是在营造一个“潘家败落,藏宝流失”的假象,让大盂鼎、大克鼎能够“暗度陈仓”。
潘祖年之所以急于离开北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尽快将大盂鼎、大克鼎带出“虎狼之口”。当世之时,金石之学大盛,清朝官宦、文人多有青铜器收藏之癖。皇都之中,权臣贵胄众多,对大盂鼎、大克鼎垂涎已久的大有人在。比如清末重臣端方。
端方也是清末著名的收藏、金石大家。与大克鼎一同出土的另一件重器小克鼎,当时已在端方手中。潘祖荫在世之时,端方就曾多次欲购大盂鼎为己有,无奈出价再高,潘祖荫也绝不割爱。
潘祖年年纪轻轻,虽未为官,亦深知官场险恶。兄长离世,在北京再无庇佑,只能携带着所有藏品回乡避祸。
潘达于曾回忆,当年各种藏品足足装了四艘船。古人形容藏书数量之巨的“汗牛充栋”,想来也就是这样的光景吧。
潘祖荫穷尽家财收藏的大量青铜器和珍本古书,是出于一个文人对古文化的痴狂。潘裕达认为:“潘祖荫收藏青铜器的最终目的,是因为他醉心于古文字学研究,绝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古玩收藏或是什么投资。不然,以潘家藏品的价值来说,应该是‘富甲天下’,而不是‘藏甲天下’了。”
在潘祖年后来编著的《潘祖荫年谱》中可以看出,潘祖荫在世时,虽对自己所藏极为珍视、自豪,却从不私藏。“每得一器,与同好者切磋研究,图状释文,以传后世。”常与商榷者,有周孟伯、张之洞、王懿荣、吴大澂等,皆清朝末年有金石之癖的一代大吏。
而潘祖年接管了这批海量的文物珍品后,深恐藏品“露富”而被贪佞图谋,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
潘祖年携宝归乡之后,起初住在祖父潘世恩留下的祖宅之中。潘世恩曾高中状元,官至清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身后育有四子,潘祖荫、潘祖年即三子潘曾绶之子,在潘家谱系中称“老三房”。
潘家家族庞大,在苏州府邸甚多。钮家巷的潘世恩故居最为门庭显赫。潘祖年始终顾虑这栋大宅门庭显赫,太过惹眼,不久又搬到了南石子街,“老二房”一座空闲的宅院之中。自此,潘祖年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终日与满屋的青铜器为伴,藏身古籍故纸堆。
潘祖年对“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把持极严,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世人皆传“潘家有宝”,却无人能一睹真容。潘祖荫的故交王懿荣、吴大澂等人,对潘家藏品其实非常熟悉。但是到了潘祖年这里,哪怕仅仅是借金文拓本一阅,也不能如愿。
吴大澂之孙吴湖帆,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书画大家和收藏家,娶潘祖年之女潘静淑为妻。据说,有一次吴湖帆到丈人家中的储藏室外,向着门缝里张望了一下,事后潘祖年就吩咐人用纸把门缝窗缝统统糊上。
对家人尚且如此,对付外来的压力可就更难了。
大盂鼎和大克鼎被转移到苏州不久,1906年,对二鼎垂涎已久的端方竟然也来到了江南。这时的端方,权势更非早年所比。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西安时接驾有功,端方受到重用,历任河南、湖南封疆大吏。1905年,清政府为挽救危局,“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列强宪政。端方就是“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归来,端方所编《欧美政治要义》,被认为是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
“出洋”归来端方再获赏识,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主理大清一朝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对流落到自己势力范围的大盂鼎、大克鼎,端方自然不肯放过。
端方对青铜器的嗜好,并不亚于当世任何收藏家。就是在两江总督任上,端方得到了“海内三宝”的另一件——毛公鼎。
关于此事,史料上有这样的记载:毛公鼎原是北京的另一大收藏家陈介祺所藏。在收藏界,陈介祺与潘祖荫齐名,史称“南潘北陈”。陈介祺对其他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世,印成目录,唯有对毛公鼎,深锁密藏。陈介祺1905年病故后,端方查访到毛公鼎的下落,他倚仗权势派人至陈家,限三日交鼎,强行买走。
当时的潘家与陈家境况是何其相似,大盂鼎、大克鼎似乎是逃不出端方的手心了。然而权倾一时的端方却在潘家碰了一鼻子灰。
潘祖年曾对后人回忆过,端方几次三番地找到他,图谋盂、克二鼎,或曰重金购买,或曰借几日观赏,乃至仅仅要求亲眼看一次。而潘祖年的答复始终就是两个字:“没有。”
这样的答复就能令端方善罢甘休?只怕没人能够相信。对此,潘裕达这样分析:潘家虽然家道中落了,毕竟曾经数辈为官,朝野之上故旧至交众多。端方虽然位高权重,论起辈分还要算潘祖荫的门生,再加上对潘祖荫一脉的政治人物终归有所忌惮,一时倒也不敢像对陈家后人那样用强。
“这只能勉强敷衍一时。真正让大盂鼎、大克鼎免被巧取豪夺的,是端方的意外之死。”潘裕达说。
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政府急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结果造成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发动起义,辛亥革命首役成功。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土崩瓦解。
而端方刚入四川,所率新军就发生兵变,被部下刺杀。
端方有生之年,最终连大盂鼎、大克鼎的真容也未得见。
端方之死,让潘家珍藏的最大威胁得以消散。然而,另一团阴影却像诅咒一样笼罩着潘家。
潘氏“老三房”一脉,潘祖荫终身未育,潘祖年有两儿两女,但两个儿子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后来从“老四房”过继了两个男孩,结果又都夭折。潘祖年年届40岁时仍膝下无子,而当时族中侄儿一辈尽皆成年,潘祖年就从“老四房”嗣进了一个孙子,取名潘承镜。潘承镜成年后娶苏州名门丁氏之女为妻。可是婚后数月,潘承镜又染病身亡,同样没能留下子嗣。
接连发生的家门不幸,让颇为神秘的潘家又蒙上了一层诡异。时人皆传,潘家血脉难继,是因为家藏的青铜器太多、阴气太重所致。
这种怪力乱神的联系、解释,在当时被传得神乎其神,言之凿凿,成了笼罩潘家几十年的一道梦魇。
“潘家年轻夭亡的儿孙确实不少,但放眼当时的中国,也不算稀奇。要怪只能怪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动荡乱世。”潘裕达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清末乱世,这个数字无人统计,但料想也不会超过35岁。
潘裕达告诉记者,就是因为潘家的收藏太过神秘,才被人与种种不幸扯上了联系。实际上,潘家的人丁零落,并不独独发生在青铜器收藏甲天下的“老三房”。大房、二房、三房在祖字辈之后,都先后失去了直系血脉,不得不从“老四房”过继子嗣。从血缘上来讲,今世的潘氏家族都是“老四房”的后代。
而直接收藏、保管着那些青铜器的潘祖荫和潘祖年,分别享年60岁和56岁,在当时已经算得上长寿了。
1926年,潘祖年逝世,留下的沉重家产只能由一个弱女子独立支撑。这个女子,就是时年仅20岁的潘达于。
潘达于即为潘祖年继孙潘承镜之妻,才过门数月就成了寡妇。“老三房”中,当时只剩潘祖年夫妇和这个寡孙媳妇三人。
潘祖年疼惜孙媳年轻守寡,视其为孙女一般,并让她改姓了潘。而且,潘祖年从此不再过继孙子,而是由潘达于出面,为先夫立嗣子,也就是潘祖年的过继重孙潘家懋。这样做,实际上就是确定了潘达于作为孙辈的家业继承人。
而潘祖年的离世,把潘家收藏的总数永远带离了人间,“攀古楼”、“滂喜斋”中所藏文物、珍本究竟有多少、有哪些,从此成了不解之谜。
潘裕达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先人的收藏,但始终得不到答案。他告诉记者,祖荫公晚年曾辑有《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但未及将所有藏品辑录就去世了。饶是如此,书中所载亦有林林总总数百器。除大盂鼎、大克鼎之外,尚有著名的史颂鼎、邵(lǚ)钟四、郾侯鼎、夫舍鼎、季余鼎、祖乙卣(yǒu)、休敦、季良父等等,蔚为壮观。
潘祖年继承了兄长的收藏之后,“谨守护持,绝不示人”,20余年从不对外吐露半字。潘祖年编撰了《潘祖荫年谱》,按理应该是对这些藏品进行过系统整理、清点,但没有留下详细谱录就撒手人寰。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顾廷龙,娶潘祖年堂侄女为妻,是极少数几个能得到潘祖年信任,有机会亲眼目睹潘家收藏的人之一。顾廷龙曾靠年轻时的记忆,作过一篇《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叙》,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潘家青铜器收藏最详细的统计:
“潘氏器,未有人编其目,余亦就所见拓本而钤有其藏印者,录为一册,计四百数十器,秦、汉物及其杂器则尚未在焉,洵足为藏家之冠。至所藏总数,未由访悉,惟褚礼堂尝谓藏六百余品,则余所辑录者三之二耳,余者得非即秦、汉物及其他杂器也耶?”
可见,顾廷龙也未能得见潘家藏品全貌,只能大致估计其总数。这一点在潘达于的回忆中也有所印证。
潘祖年当年居住的南石子街旧宅,是一个“跑马楼”。所谓“跑马楼”,指的是四周都有走廊可通行的楼屋。宅院共有三进,潘家的收藏就保存于第二进的房子中。据潘达于回忆,当时青铜器放满了一大间加一隔厢,字画卷轴典籍堆放在另外一间一隔厢内。
顾文中所说的“褚礼堂”位于这栋房子的二层,只摆放着数量众多的小件青铜器。而大盂鼎、大克鼎等重器并不在此处。潘祖年为这两件鸿宝专门打制了两只大木柜,平时柜门严锁,放置在一层屋中。看上去和一般的衣柜无异,而外人根本不知里面放的竟是两只旷世宝鼎。
1926年潘祖年病故,潘家懋年仅4岁,年纪轻轻的潘达于不得不挑起侍奉好婆(潘祖年的续配祁氏夫人)、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1933年,祁夫人又去世,潘达于身边只有家懋、家华一双过继儿女。
偌大的庭院,孤儿寡母三人守护着几屋子随时被人窥视的文物财宝,潘达于的压力可想而知。
潘达于没有文化,自己没有能力对浩荡藏品进行整理、清点,又不敢借他人之手,她能做的,就是把藏宝的几间屋子尽皆锁闭,至于藏品总数,潘达于终生都不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潘家向国家捐献了大量藏品。原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国青铜器研究泰斗马承源曾对潘达于老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家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这句话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鸿宝重现 克保永久
1951年7月,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引发举世轰动的捐赠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寄信人,正是已经守护了大盂鼎、大克鼎二十余年的潘达于。
1951年历来被看做是大盂鼎、大克鼎第二次出土的年份。而潘裕达告诉记者,实际上,此时距两件宝鼎第二次出土已经过了7年。
1944年,潘家旧宅堂屋八仙桌下的方砖地面忽然塌出了一个大洞。原来,当年埋鼎时太过仓促,木箱就是从市场上买的原木,从中间劈开后草草钉成。在地下埋藏7年后,木料腐烂,连泥土带方砖都塌了下去。
潘达于急忙让儿子家懋和木匠把两只大鼎重新挖了出来。
当时苏州仍被日伪政权占据着,两只大鼎被悄悄安置在潘宅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房间锁死,再不进人。两鼎就这样又秘密保存了7年。
值得一提的是,原被端方所藏的毛公鼎,在端方死后被后人售卖,几经流转,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历经劫难,几次被典押、质卖,险被日军掠走。但终被叶恭卓、叶公超、陈永仁等几位收藏家、实业家保护了下来。1946年,沪上巨商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而毛公鼎重现世间之时,与之并称“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虽然也已再次出土,守护者潘达于却选择了秘而不宣。直到1951年。
潘裕达说:“其实国民政府要员在抗战之前和之后都找到过好婆,动员她献宝,但她一直不为所动。抗战胜利之后,好婆主要居住在上海。在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她亲眼看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天壤之别,这才决定把宝鼎捐了出来。
1951年9月,在潘达于的指点下,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等人搬开角落中的杂物,微尘轻扬中,宝鼎重光再现。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文化部特颁褒奖状:“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
这张奖状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50年。
而对人民政府奖励的2000万元(相当于2000元)奖金,潘达于却没有收下,她又给上海文管会写了封信:“查上项古物归诸人民,供历史上之研究,正欣国宝之得所,乃蒙政府赐给奖状举行典礼,已深感荣幸,今又蒙颁给奖金,万不敢再受隆施,恳请收还成命,无任盼祈之至。”最后,潘达于将这笔钱捐献抗美援朝。
虽然潘家先代曾是钟鸣鼎食的权贵名门,但捐鼎时,潘家经济已不宽裕。执掌潘家的潘达于知道这两尊鼎价值连城,但她从没拿藏品去“换生活”。那时潘达于和女儿潘家华在上海相依生活,女儿在学校教书,每月70元收入,而潘达于则走进了里弄生产组,当了一名普通劳动者。
而在捐出盂、克二鼎后的几年里,潘达于又数次捐出了家族中收藏的所有珍贵文物。细细点数潘达于家里的收条,仅上海博物馆一地收藏的文物就达400多件。如果按文物市场的价格计算,将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但是,文物真正的价值和潘达于老人的义举一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遥相呼应。
2005年,潘达于老人百岁寿诞,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大盂鼎、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重新聚首。这是上博为给百岁人瑞潘达于祝寿而举办的回顾特展。当天下午,身着棕色缎袄,脚穿新绣花鞋的潘达于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展台,围着栏绳走了大半圈。“好婆后来说,我为俚笃(苏州方言,它们)寻着好人家哉。”潘裕达回忆道。
2007年8月,潘达于走完了她102载的传奇人生,与世长辞。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但上海博物馆刻着捐赠人姓名的大理石墙上,“潘达于”高高在上,永远和盂、克二鼎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