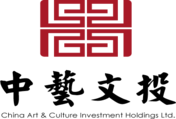全球化视野下的公众考古学新发展
2015-04-11 22:59:10 作者:刘焱鸿 来源: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已浏览次
公众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反映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式。自1972年“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概念的首度出现及使用,其学科发展已有四十余年,至今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公众考古学主张让大众社区进入考古学场域,从而使之获得考古学研究“权力”,主要涉及到阐释权、教育权、开发权和保护权。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公众考古学一方面因应挖掘、保护和传播本国(本地)文化的“本土化”需要,从而得到比较广泛的大众认同,另一方面,遵循着全球化的规律,公众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也由学科中心向全球辐射。然而,公众考古学的理论传播及其理论指导下的“考古”实践在全球各地表现出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的特点。特别是在多样性方面,东亚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公众考古学的最初定义及关注范畴
公众考古学的定义是什么,至今仍没一个确切的定论。1972年,查尔斯·麦克基姆(Charles McGimsey)出版了《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第一次提出了“公众考古学”的概念。[1]它最初的含义是: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考古遗存面临各种被破坏的威胁,考古学家有义务和责任进行记录和保护,并且必须得到公众的支持。这一观点如今仍然在美国广泛流传。这是因为美国的公众考古学天然地与政府所关注的文化遗产管理(CRM)事业联系在一起。但在世界的其他地区,这个术语则添加了更丰富的内涵。[2]
创刊于2000年的《公众考古学》,是第一本该学科领域的专业杂志,当中列举了公众考古学应关注的主题,包括:考古的政治策略、教育与考古、政治与考古、考古与古物买卖市场、种族与考古、考古中的公众关注、考古与法律、考古经济、文化旅游与考古等内容。在当时,公众考古学已经关注到专业考古学与公众之间如何沟通、调和、融合的多样性问题,同时也希望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总结出公众考古学多样性的实践经验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尽管如此,公众考古学始终没有取得与一个成熟学科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学科的内容包罗万象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例如,在解释公众考古学家到底是干什么的时候,答案就五花八门:有的认为是考察考古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有的认为是在公众之中进行考古学的研究,还有的认为是为公众保护考古遗存,等。要去解释公众考古学是一种学科研究还是实践活动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且绝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非“学术问题”,从根本上说它只是考古学科专业实践活动中居于边缘地位的细枝末节。有学者指出,公共考古学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上而下的,“公共”是作为引导公众认识和理解考古的社会权威或职业权威的化身,诸如国家;第二个阶段则是自下而上的,“公共”是作为场域的公共,[3]诸如社区民众。因此,与公众考古学如影随形的,是以生态博物馆为号召的新博物馆运动和关注草根阶层的社区考古学。这些思潮背后,则是后殖民主义运动和多元主义等带动的整体反思。换而言之,公众不再是统一发声的笼统化身,而是转变为形形色色个性鲜明的个体综合。公众考古学家也不再是职业知识的传道士,而成为了真正与民众结合的同盟体。
根据全球各地的公众考古学发展情况来看,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地的公众考古学成功案例最多,反响最热烈,而在亚洲和非洲则缺乏足够多的经典个案,反响相对平淡。[4]受到考古学学科范式转型的影响,公众考古学在各地区的生成都具有自身的历史特色与地域特色,而这恰好与公众考古学在全球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化体现密切相关。例如,在当代东亚地区,中国、日本与韩国的公众考古学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主义传统基础,又分别应对不同的社会发展情状,从而衍生出不同的视角和表现形式,解释传统考古学所无法触及的问题。
二、当代中国、日本及韩国的公众考古学发展比较
在当代东亚国家的场域之中,公众考古学尚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形成过程之中,无论是研究主题、实践策略还是作业流程,甚至是学科定位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考古学研究上,公众考古学与多元的、反思的考古学视角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传统的考古学研究进入大众视野,揭示和弥补传统考古学研究的疏漏和表达误区。[5]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学者界定当代东亚三国即中国、日本与韩国公众考古学发展的关键活动或者事件。因此,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对这三国的公众考古学发展个案进行梳理及初步讨论,有助于理清当今东亚地区的学科发展趋势,亦有助于丰富学科理论探索的实践个案。
(一)中国公众考古学关注普及知识和公众介入
公众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其说是学界对新的学科分支的兴趣,还不如说是中国考古学大众化历程的起点。如何界定公众考古学中的“公众”,是理解中国公众考古学发展的关键所在。有学者就曾指出,公众之于西方世界的公共决策,在中国更多理解为社会民众。[6]其次,西方的公众考古学被纳入到文化资源管理范畴,而中国的现状则是以民众的考古知识普及和理念普及为主。高蒙河就提出了中国考古学的大众化历程经历了普及知识、理念提出以及普惠大众的文物保护和利用三个阶段。[7]简而言之,当代中国的公众考古学可区分为普及知识型和公众介入型两种主要取向。
普及知识型的公众考古学主要由职业考古学家发起,树立考古学大众化的理念。通过撰写科普读物,指导拍摄科教纪录片,参与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等方式,将专业的考古资源传达给公众,从而增加社会对考古学的了解。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非公众考古学的学科表现,更多的是属于单一型的考古传播活动。
公众介入型的公众考古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蓬勃发展。2003年在“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上,学界初步达成了“全面结束孤芳自赏,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共识。从政府层面讲,以国家文物局为倡导,如每年进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由公众通过网投、票选决定,增加了公众对于文化遗存的了解。从考古职业机构来讲,如北京大学设立了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公众考古发展促进中心,订立章程,对社会开放,提供相关法律法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信息咨询。此外,网络成为了传播互动活动的新兴力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复旦大学的知名学者利用博客与网友进行互动和知识答疑,部分实现了利用现代技术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的目的。
毋庸讳言,中国的公众考古学实践更多体现的是与“众”的唱和。但是,考古学的公共意义并非是职业考古学家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相反,是公众如何更大程度地直接参与考古。作为一个历史悠长、文化深厚的东方国家,中国的公众考古学天然地与历史学、博物馆活动联系在一起。对中国民众而言,对话和沟通远比展示和教育的模式更为有效。与西方的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核心理念不同,中国的公众考古学具有其独特的发展特色。
(二)日本公众考古学以考古遗产管理为中心
在考古学、有形的文化遗产以及社会民众之间,日本学界确立起一种独具特色的考古遗产管理体系。二战战后的经济腾飞,经费和资源投入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朝野对历史遗迹发掘的热情和兴趣。考古遗产管理(AHM)中心的成立与兴起,正是当代日本学界在公众考古学发展中的缩影。[8]二战后的头二十年,国家的研究机构,地方博物馆以及大学院校等都致力于考古发掘,成为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的先声。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开始建立起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的半辖治机构,称之为“地下文化遗产”中心。建立这种半公共类型机构的最大原因是经济因素的考虑。地方政府一方面避免了过重的财政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因外来基金支持的比例决定考古发掘的预算和聘用考古学家的人数、发掘规模等。由于其设立迎合了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各种保护机构特别是“地下文化遗产中心”增长迅速,从1965年的8所,增至1997年的7111所。这成为了国家层面考古遗产管理中心的深厚研究基础。
从年代关系上看,1953年日本冈山(Okayama)的冈村发掘项目是年代较早的公众考古学发掘范例,也被学者引述为公众考古学在日本成熟的标志之一。参与发掘的约有一万人次,包括了:职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村民,中小学校教师以及学生。[9]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可以视作社区考古学(community archaeology)在东亚地区发展的一个先例。[10]无论对研究者还是村民而言,这是第一次的联合尝试:在本地历史和国家历史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后者正是“人民的历史的运动”(People’s History Movement)的真实写照。
从机构发展上看,考古遗产管理中心的迅速发展,为公众植入考古学领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著名的大型考古遗址,如弥生时代佐贺县的吉野里遗迹,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前往参观访问,这也让地方政府意识到开发考古遗址可以作为地方旅游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持续的修整、展示和更新也能吸引到足够的游客。
以考古遗产管理中心为主体的日本公众考古学发展体现了四种主导理念:公众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历史观、考古学研究训练的主要场所是机构而非大学、“考古学家”不仅仅是挖掘者,还是保护者和管理者,以及考古遗存保护和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究其根本,在于日本学界对“同文同种”(we are the same)的认识。关注遗存物质的社会表达成为考古遗产管理中心的重要工作。与其说中心的考古工作人员是“考古学家”,还不如说他们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与中国的知识普及型为主导的特色相比,日本的公众考古学更强调在“专业”的理论延伸。
(三)韩国公众考古学聚焦于大众化导向的教育项目
尽管公众考古学这一观念在整个世界已经被广泛认识,但是韩国学界对此的认可并不热衷。这与韩国在东亚考古学中所处的微妙位置不无关系。韩国的本土考古学发展在东亚地区未能占到重要的一席之地,与比邻的日本相比并不突出。如何彰显本国的文化传统,为本国民众创设更多了解认知的教育机会,成为韩国公众考古学择选大众化导向的教育考古项目的最大动力。
近二十年间,通过不同范围、层次、形式和内容的实践计划,促成了韩国民众对公众考古学的接纳,以及参与。在韩国,公众考学教育项目根据主导者的不同,可区分为如下的四种类型:由职业考古社团从事的项目;由各层次政府考古计划所开展的项目;大学以及博物馆所开展的项目;私立机构为志愿者和学生所提供的项目机会。
以上的四种主导者,国家博物馆扮演了最为核心的角色。第一次的有益尝试是1977年由韩国国立博物馆倡建的“博物馆学院”。其宗旨就是为了鼓励更广泛的民众了解自己国家传统文化和历史的通识,也为终身教育提供更加多元的选择机会。[11]这一项目每年为400名参与者提供50场不同类型的讲座,涵括韩国史、人类学、考古学以及艺术史,此外还有五次的古代遗迹参观。大部分参与项目的人群集中在25-59岁之间。在完成项目学习后,他们有机会成为博物馆的导览员。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机构——包括公立和私立的博物馆以及大学——开始建立类似的“博物馆学院”(museum college),并且衍生出更多不同类型的主题计划。例如:使用通俗读本进行考古知识的普及教育,用艺术表达的方式传递考古信息,而最重要的现场沟通,则是在遗址建立良好的公众关系,从而实现知识信息的理解。
在韩国,本土社区的观念是了解区域历史,增强文化自豪感的重要切入点。然而,在这种民族主义情感被过分渲染或者刻意放大时,公众身体力行的参加反而造就了一种假象。在对遗迹阐释作出选择的同时,事实上也可能因此失去对正确诠释作出选择的机会。这一困惑不仅见于韩国,同样见于中国和日本,可以视之为东亚地区公众考古学的共同问题。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日本以及韩国地区的公众考古学发展,呈现了东亚地区学科发展的探索。这三种实践模式虽然并非孤例,但因应东亚国家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社会情状而表达出不同的实践诉求。
三、当代公众考古学的多元化发展
当代公众考古学的发展表明,学科的专业化与学科根植于社会发展并不矛盾。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环境,改写了学科的研究取向。公共遗址的对外展示,不仅受到来自本土民众、政府、外来游客、媒体、研究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还要兼顾沟通、保护、展示、研究等功能。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不仅打破了原有的知识获取来源和途径,建构了人类新型交流的平台,也为公众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祖布罗(E.Zu-brow)就曾指出,随着考古学研究不断使用各种信息技术,职业考古学家、其他专业学者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模糊。[12]民众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可以主动获取文化资源的相关信息,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诠释和分析资源,“主动获取”是公众考古学价值取向转变的重要推动力。
此外,公众考古学对考古学研究最直接、最显著的改变,是多元观念的采纳,揭示传统考古学所不曾关注的现在时态以及将来时态。福克纳尔(N.Faulkner)通过分析精英考古学和草根考古学之分,希望唤起人们对考古学社会属性问题的关注。多元化观念不仅体现在考古学学科,而是广泛分布在整个社会科学当中。从传统的研究过去,转变为研究过去与现在、未来如何连接。通过分析中国、日本以及韩国这三个东亚国家的个案,我们发现:以知识普及为主流,以遗产管理为中心,以教育项目为导向的三种实践模式,揭示了与公众考古学在欧美国家、地区发展迥异的特色。这为公众考古学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践个案。
参考文献:
[1]Ezra B. W. Zubrow. Digital Archaeology:A History Contex[tM]∥ed. By Thomas Laurence Evans and Patrick T. Daly. Digi-tal Archaeology:Bridging Method and Theory. Reutledge Press,2006,11.
[2] Choi,M. J. Kukmingwa Hamke Hanun Saenghalsokui Kogohak[Archaeology together with the Public in Daily Life][M]∥ed.by Daehan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Center. Kogohakun Siminsahoesokeseo Soomshigo Innunga?[Does Arcaheology Really Ex-ist for Our Society Now?]. Daehan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Center,Gwangju,2009:2 - 8.
[3]徐坚. 社区考古学:文化遗产管理还是考古学研究[J]. 东南文化,2011(5):38 - 44.
[4]Fawcett,C. P. ,Nationalism and Postwar Japanese Archaeology[M]∥ed by P. Kohl and C. Fawcett. Nationalism,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5:232-246.
[5] Okamura,K. And Matsuda,A.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Management in Japan[M]∥ed. By P. M. Messenger and G. S.Smith.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A Global Perspectiv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Florida,2010:67 - 80.
[6]高蒙河,郑好. 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J]. 东南文化,2013(6):24 - 29.
[7] Tao Wang. “Public Archaeology”in China: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M]∥ed. By Katsuyuki Okamura and Akira Matsuda. New Perspective in Global Public Archaeology. Springer,2011:43 - 50.
[8]伊恩·霍德,司各特·哈特森. 阅读过去[M]. 徐坚,译. 湖南:岳麓书社,2005:87 - 91.
[9]Yvonne Marshall. What is community archaeology?[J]. World Archaeology,2002,vol. 34,no. 2:212.
[10]徐坚. 我们这个时代的通俗考古作家呢?[N]. 东方早报,2013 - 06 - 3(5).
[11]Nick Merriman,eds. Public Archaeology[M]. New York:Routledge,2004:107 - 190.
文物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一、凡本站中注明“来源:文物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版权均属文物网所有,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文物网”,并附上原文链接。
二、凡来源非文物网的新闻(作品)只代表本网传播该信息,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见后30日内联系邮箱:chief_editor@wenwuchina.com
月度排行
新闻速递
- 2021年度文物保护示范工程公布
- 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稿考论
-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张同禄80华诞纪念典藏展开幕,景泰蓝《盛世同路》引...
- 为盛世献礼,与第一大党同路!景泰蓝《盛世同路》在沪...
- 国之重器景泰蓝《和平颂宝鉴》入藏敦煌博物馆
- 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八十华诞纪念典藏展盛大开幕,《盛世...
专题视点MORE
原创推荐MORE
- 文物网培训中心
- 美好时光
- 大家鉴宝—老窑瓷博物馆公益鉴宝活动圆满举行
- 曜变之旅
- 菖蒲河园,一袭釉色染枝头
- 龙泉琮式瓶
- 盛世风袭北京城,金秋月览长安客(下篇)
- 阿富汗珍宝展之:石膏盘上的希腊神话
- 秘色出上林
- 阿富汗珍宝展之:恒河女神雕像